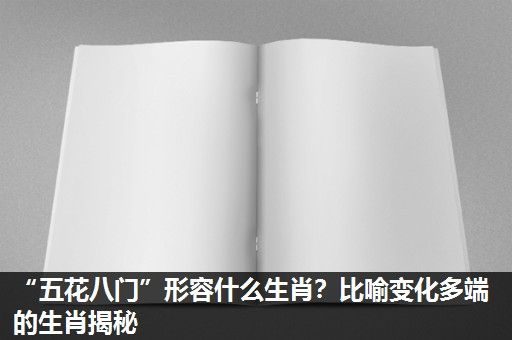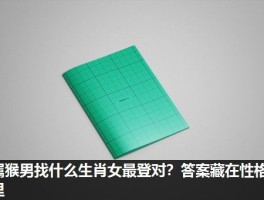公司最近几个项目组重组,人员打散了重新排列组合,办公室里一时间有种兵荒马乱的活力。新搭档,新流程,新脾气,得重新磨合。午休时几个同事凑在一起喝咖啡,不知谁感叹了一句:“这回可真是五花八门了。”大家都笑。我也笑,但脑子里却忍不住拐了个弯——这“五花八门”,形容局面之纷繁、样貌之各异,固然贴切;可要是往深处想,往人身上想,什么样的人,骨子里就自带这种“五花八门”的属性,甚至乐在其中呢?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属猴的朋友。不是泛泛地说猴子聪明机灵,那太没劲了。我认识一位老陈,就属猴。有次参加一个挺尴尬的饭局,几路人马互不熟悉,话题有一搭没一搭,冷场像雾气一样弥漫。老陈是中途来的,进门三分钟内,他就像一滴活水掉进了油锅,滋啦一下气氛就活了。他能跟甲方聊两句最新的行业趋势,转头又能接上乙方小伙子的游戏梗,甚至还能跟一位一直沉默的年长者,聊起某种特定兰花的养护心得。他说话时眼神亮亮的,手势丰富,仿佛每一个在场的人,他都能迅速找到对应的频道,无缝切换。那是一种令人叹为观止的社交柔术。
但你说这是纯然的天赋吗?有一次散局后,我跟他同路,他脸上那种鲜活的神采褪得干干净净,只剩下一点淡淡的疲惫。他点了根烟,说:“哎,就是个气氛调节器,没办法,见人就得说人话。”那一刻我忽然觉得,属猴人的“五花八门”,或许是一种高度发达的情境适应力,一种近乎本能的表演欲。他们像水,没有固定的形状,却能迅速填满任何容器。这是生存的智慧,让你在任何环境里都如鱼得水;但反过来说,这是否也意味着,他们很难有某个坚硬的、不变的“内核”?他们的“变”,是主动的嬉戏,还是被动的迎合?我对他欣赏之余,总保留着这么一点矛盾的疑问。
话又说回来,“变”未必都是猴那样外显的、热闹的。另一种“五花八门”,静水深流,属兔的朋友是典型。我们常说的“静若处子,动若脱兔”,真是绝妙的概括。我部门里有个姑娘小敏,属兔,平时安静得像只蘑菇,坐在工位角落里,说话轻声细语,交给她的任务总是完成得细致妥帖,但也看不出什么锋芒。大家都觉得她是个挺好的执行者,仅此而已。直到有一次,一个棘手的方案讨论陷入僵局,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直沉默的小敏忽然开口,条分缕析地指出了几方逻辑的漏洞,然后提出了一个我们谁都没想到的、绕开死胡同的路径。她说话还是不紧不慢,但那个方案大胆又精妙,听得我们一愣一愣的。
后来我私下问她,怎么想到的。她有点不好意思,说:“其实你们吵的时候,我就在脑子里把几种可能性都推演了一遍,发现都不通,就只能换个角度试试看了。”你看,这种“变”,不是猴子那种即兴的、外向的应变,而是一种内在的、策略性的多线程思考。兔子的“五花八门”,藏在它极度警觉的感官和敏捷的反射神经之下。那温顺的外表,可能只是一种精妙的伪装,或者说,是一种节能模式。他们只在必要时,才亮出那种令人意外的、爆发式的“脱兔”姿态。这种多变,是隐藏的实力,也是一种深刻的自我保护。你永远不知道,在那副安静的表象下,她已经演练过了多少种可能。
当然,像蛇的幽邃善谋,鼠的机敏善藏,多少都沾点“变”的边。但以我的观察,蛇的变,是谋定而后动的轨迹,是冷血的耐心;鼠的变,是危机驱动的本能,多少带点仓皇。猴与兔的“变”,更有一种主动的、甚至带着点审美意味的灵巧在其中。
想着想着,我发现自己琢磨的,或许早已超出了生肖的范畴。我们谁不是“五花八门”的呢?在公司是员工,回家是子女或父母,在朋友面前是损友,独处时或许又是另一个陌生的自己。社会角色像一件件不同场合的外套,我们熟练地穿上、脱下。属猴的老陈,可能渴望着一刻不必应酬的彻底安静;属兔的小敏,或许在某个我们看不见的领域,正兴致勃勃地主导着一场风暴。我们都在适应,在切换,在扮演,这本身就是现代人生存的常态。
那么,“变化多端”到底是优点还是缺点?年轻时,我或许会欣赏猴的灵动,觉得兔的谨慎不够痛快。但现在,我反而觉得,能“变”是一种可贵的能力,但知道何时该“定”,何处是“本”,或许更是一种难得的修为。就像我这份写稿子的工作,面对不同的题材、不同的平台、不同的读者,笔调也得“五花八门”,时而严肃,时而调侃。但在这所有的“变”之下,总得有点不变的、属于“我”的东西撑着,那可能是一些基本的价值判断,一种对文字本身的敬畏,或者仅仅是一点不愿彻底妥协的固执。没了这点“不变”,所有的“变”就成了浮萍,成了无根的表演。
咖啡喝完了,同事们各自散去忙活。我看着办公室里这些重新组合、正在彼此试探的新团队,忽然觉得,用“五花八门”来形容他们,或许并不只是因为背景或性格的差异。更深处的原因,是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揣着一个复杂的、动态的、尚未被完全定义的小宇宙。当我们带着自己的小宇宙,去碰撞另一个小宇宙时,所产生的光谱,自然是炫目而混乱的。生肖像是一个模糊的、好玩的坐标,给我们提供一点聊天的谈资和观察的起点,但真要理解眼前这活生生的、具体的人,恐怕还得放下那些简单的标签,去看见那标签之下,真正“五花八门”、流动不息的生命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