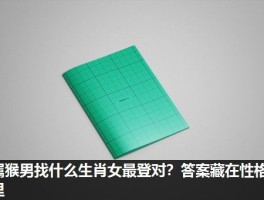整理旧书的时候,翻出一本纸张脆黄的家谱手抄本。手指抚过那些用毛笔小楷工整记下的生辰,目光停在了一位叔公的名下:“丙寅年腊月生。”心里默算了一下,丙寅年,那便是1926年了。再过两年,到2026年,这位我印象中总是穿着深蓝布褂、沉默寡言的老人,若还在世,该是整整一百岁了。
话说回来,这生辰的算法,如今常让年轻人迷糊。1926年1月1日出生的人,生肖可不属虎。得看春节。那年的春节来得晚,是公历2月13日。所以,在2月13日之前出生的,仍算乙丑牛年;从2月13日零时起,才算正式踏入丙寅虎年。我这位叔公生在腊月,那铁定是属虎了。一只在旧年岁尾降临的虎。
属虎的人,书里总说威猛、果决。可我回忆里的叔公,以及他们那代大多数属虎的人,似乎不太一样。他们的“虎性”,不是山林啸聚的张扬,倒更像年画上褪了色的门神,威严是有的,但经了太多风雨,那威严沉静地内敛下去,化成了骨子里的韧劲。叔公话极少,年轻时经历过战乱、迁徙,中年时扛着一大家子的生计,脸上沟壑很深,眼神却定定的。我唯一记得他说过一句有点“虎气”的话,是在一次家族的小纠纷里,他并没提高嗓门,只是用烟杆轻轻磕了磕桌面,说了句:“这事,就这么定了。”满屋子嘈杂竟立刻静了下来。那一代人的权威,不靠音量,靠的是岁月磨出来的重量和一种不言自明的责任担当。他们的勇猛,全用在对付生活这本厚书上了。
那么,到2026年,这位1926年出生的虎,该是多少岁呢?按现在通行的周岁算法,过了生日才算,那便是实打实的100周岁。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数字。但我们老辈人心里,还装着另一套算法——虚岁。虚岁啊,说来有趣,它一落地就给你算上一岁,接着再把你在娘胎里那近十个月的光阴,慷慨地赠予你,当作“第一年”。所以到2026年春节,一开年,他的虚岁便是101了。我个人一直觉得,虚岁算法里这份“提前给予”的年龄,充满了东方式的暖意与期许,它承认你从存在那一刻起,就已经在生命的长河里跋涉了。虽然年轻人总嫌它麻烦,但它让生日不仅是庆祝“来到”,更是纪念“走过”。这多出来的一“虚”岁,不是糊涂,是一份对生命历程早早开始的、庄重的认可。
百岁,是人瑞了。我见过几位乡下的百岁老人,他们的时间感似乎和旁人不同。像一棵老树,年轮密密麻麻,反而显得格外宁静。他们对具体哪年哪月常常模糊,但对几十年前的某场大雨、某顿食物的滋味,却记得真切。长寿到那个份上,数字本身已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具躯体所承载的记忆,厚得像一部无声的史诗。1926年,那是什么光景呢?那是一个大时代剧烈搅动的开端之年。那一年出生的小虎崽,睁开眼看到的世界,与他百岁时回望的世界,怕是连地貌与星图都迥异了。他的一生,就是一部活的百年史。想到这里,我对着家谱上那个冰冷的名字,竟生出些莫名的感慨。我们计算他的生肖,核算他的年龄,真的只是为了知道“属什么”和“多少岁”吗?
或许不全是。这更像一种定位,一种在浩瀚时间和纷乱家族图谱中,为某个生命寻找坐标的努力。通过“丙寅虎年”这几个字,他与六十年前、一百二十年前的同肖者产生了神秘的链接;通过“百岁”这个节点,我们得以度量个体生命与世纪长度的重合。在一切都快得让人眩晕的今天,这种缓慢的、带着点迂腐气的计算,反而成了我们抓住一点确定性的方式。我们在算的,或许不是他的岁数,而是我们自己与根脉的距离,是对“长久”二字的一点具体想象。
合上家谱,窗外已是薄暮。隔壁传来孩童清亮的笑声,那是属于又一个崭新生肖的、鲜活的生机。我忽然觉得,那头沉默的、跨世纪的“虎”,与这啼声,在某个看不见的维度里,完成了一次交替。时间就是这样,它用生肖一轮轮地记着账,冷酷又深情。算清楚了,心里便好像踏实了一点,仿佛那流逝的,总算被什么东西轻轻地托住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