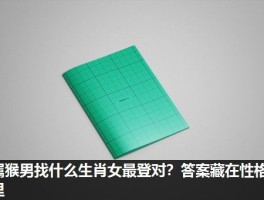11月25日国际消除对妇女暴力日:女性地位变迁史
上周整理书柜,指尖划过一本旧书脊时停住了。是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女性的屈从地位》,商务印书馆那版,纸张已泛黄发脆。翻开扉页,一行褪色的钢笔字:“购于1989.3.8,自勉。”那是我母亲的笔迹。1989年,她二十五岁,刚参加工作不久。在那个三月八日,她用微薄的工资买下这本一个多世纪前写就的、为女性权利呐喊的书。我把书凑近鼻尖,似乎还能闻到那股属于八十年代的、混合着油墨与期许的气味。就在这个瞬间,“变迁”二字,不再是历史书里平滑的曲线,而是我指腹下粗粝的、承载着具体生命温度的书页。
我母亲那代人,很多人觉得丈夫不动手就是好日子了。这种观念的残余,我前两年回老家时,还在一位远房姨母身上看到过。她向我诉说丈夫的冷漠和言语刻薄,我试探地问,有没有想过这是一种伤害?她愣了一下,随即摆摆手:“这算啥,他又没打我。我们这辈人,不都这么过来的么?”她言语里甚至有一丝“知足”的意味。这让我心头一沉。原来,对暴力边界的认定,本身就是一个漫长的、布满血迹与争辩的变迁史。
说起边界的拓宽,最显性的莫过于法律。从“清官难断家务事”到2016年中国《反家庭暴力法》施行,引入“人身安全保护令”,这条路走了何止千年。我翻过一些老档案,晚清乃至民国的诉状里,女性被严重殴伤,诉由往往是“伤害”,而非在亲密关系框架下的“暴力”。暴力被化约进一般的伤害概念里,其背后基于性别的权力结构便被巧妙地遮蔽了。法律的演进,像一盏探照灯,逐渐把那个黑暗的、被称为“私领域”的角落照亮。它开始命名那些曾被认为“理所当然”或“不值一提”的行为: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这不仅仅是条款的增补,更是一种社会认知的革命——它宣布,在卧室里发生的暴力,与在街头上发生的暴力,在侵犯人的基本尊严与安全上,没有本质区别。
有意思的是,当这盏探照灯光束越来越强,照出的景象也越发复杂。身体的伤痕易于鉴定,可那些没有淤青的创口呢?于是,变迁的下一个阶段,便是公共话语对“暴力”定义的扩容。经济控制、精神虐待、情感操控(现在人们更熟悉一个舶来词“PUA”)逐渐进入讨论的中心。我曾在一次女性社群活动中听一位年轻白领讲述她的经历:丈夫从不打她,但精确控制她每笔开销,嘲讽她的工作无足轻重,长期暗示她离了他便无法生存。她抑郁了许久,才恍惚意识到,这可能也是一种暴力。这种暴力不流血,却能精准地瓦解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感。它的出现,与女性大规模进入职场、获得经济能力的历史进程息息相关。当直接的物理压制成本变高或遭遇法律风险时,权力便找到了更迂回、也更“文明”的规训方式。地位看似提升了,暴力却进化了,它学会穿上西装,说着心理学语言,进行更彻底的内部殖民。
这便是我所理解的地位变迁与暴力演变之间最深刻的勾连:它是一场永不停歇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博弈。女性从“父亲的女儿”到“丈夫的妻子”,这一依附身份的松动(通过教育权、工作权、财产权的逐步获得),直接挑战了传统的支配模式。支配者于是调整策略。公开的羞辱变成微妙的贬低,身体的禁锢变成社交的隔离,剥夺嫁妆变成更复杂的金融掌控。暴力变得弥散、隐形,甚至与“爱”、“关心”、“为你好”的话语缠绕在一起。识别它,需要更高阶的意识和词汇。我有时觉得,这像一场漫长的智力与心理的对垒,被压迫者需要不断学习解码压迫的新形式。
当然,事情还有另一面。变迁也体现在反制手段的升级上。我母亲只能在书页里寻找共鸣与力量,而今天的女性,至少在理论上,可以报警、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寻求专业心理咨询、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形成舆论压力。工具多了,路径似乎也多了。这无疑是巨大的进步,是无数人抗争换来的空间。我书架上有那本《反家庭暴力法》单行本,旁边放着《性别打工人》这类剖析职场性别困境的新书。它们并立在那里,无声地诉说着战线在拉长、在细化。
但,这也恰恰是令人倍感无力的地方。法律文书堆叠得越来越高,现实中的落差却像幽深的峡谷。我想到去年读到的一个案件,在某个县城,一位女性多次报警称被丈夫跟踪、威胁,得到的回应却是“夫妻吵架我们不好管”。直到悲剧发生。纸面上的进步,如何穿透层层叠叠的、由地域差异、阶层差异、执法者个人观念差异构成的“缓冲地带”,抵达每一个具体的、有血有肉的女人身边?这是一个我常常感到困惑,甚至有些悲观的问题。更别说,社交媒体在赋权的同时,也催生了新的暴力形态:网络骚扰、人肉搜索、用数字手段进行的跟踪与恐吓。战场转移了,武器更新了,伤痕以数据流的形式出现,同样能致人死地。
坦白讲,思考这些问题时,我常有一种深深的疲惫感。变迁史从来不是单线向上的凯歌,它更像潮汐,有前进,也有回涌;有壮阔的浪涌,也有吞噬个体的暗流。我认识一位为受暴妇女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朋友,她说最沮丧的不是败诉,而是胜诉后,当事人因为经济困顿、社会支持系统崩塌、害怕报复,又默默回到施暴者身边。法律赢了,生活却输了。这种挫败感,是任何宏观的变迁数据都无法轻易消弭的。
所以,当我合上母亲那本《女性的屈从地位》,这个日子对我而言,与其说是一个庆祝进步的纪念日,不如说是一个肃静的检查站。它检查我们的法律堤坝是否牢固,检查我们认知的雷达是否敏锐,检查我们是否对那些更隐蔽的、穿着常服的暴力失去了警惕。它提醒我,地位的变迁,不是一个“从此幸福快乐”的童话终点,而是一个不断重新协商权力边界、识别新型压迫、并为此持续配备心智与制度工具的动态过程。
我母亲在1989年写下的“自勉”,或许意味着她相信思想的力量。三十多年过去了,思想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现实。但现实也以它的复杂和顽固,不断向思想提出新的考题。未来真正的挑战,或许在于我们能否发展出一种更精微、更坚韧、更接地气的智慧与实践,不仅修补法律与制度的漏洞,更能渗透进那些沉默的晚餐桌、那些冰冷的聊天对话框、那些被视为“正常”的规训与自我规训之中。路还长,且需跋涉。那本书的霉味里,有过去的叹息,也有尚未完成的、属于未来的信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