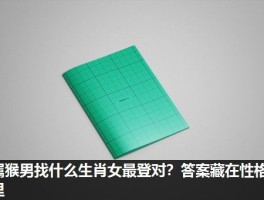下午,隔壁办公室的小王探头进来,手里捏着个手机,眉头微皱着,像是被什么简单的算术题给难住了。“周老师,打扰一下。我属马的,到2026年,我该多大来着?那是不是我本命年啊?”
我让他进来坐,顺手给他倒了杯陈普洱。茶汤在公道杯里转着圈,泛着琥珀色的光。我一边心算,一边下意识地就念叨出来:“你是……94年的?那到2026年,周岁32,虚岁可就33了。没错,丙午马年,正是你的本命年。”话说完,我自己却有点走神。时间这东西,你摊开来用加减法去算,显得特别直白,甚至有点莽撞。可当它和“属相”、“本命年”这些词挂上钩,不知怎么的,就多了层毛茸茸的、可供咂摸的意味。
要说算年龄,尤其是咱们中国人的年龄,里头还真有点小讲究。小时候,我最搞不明白的就是“虚岁”。明明生日在年底,按实打实的日子算,我才六岁半,可外婆扳着手指头一算,总说我“八岁了”。我争辩,她就笑着戳我额头:“在娘胎里那一年不算啦?落地就算一岁,过了年又添一岁,这叫虚岁。”那种理直气壮,让你觉得怀疑它就是对生命起源的不尊重。后来才慢慢明白,这虚岁啊,像是给时间这本账,预先垫上了一笔温情脉脉的“期款”。它承认你在未完全绽开时就已经存在,带着点农耕时代对生命延续的急切盼望。现在我给年轻人解释,总说这就像看一棵树,你从种子埋进土里开始算它的“树龄”,也是一种算法。当然,如今大家都习惯用周岁了,精准,和国际接轨。可逢年过节回老家,长辈们嘴里蹦出来的,依旧还是那个让你觉得自己“莫名年长”了一两岁的数字,仿佛那是你永远甩不掉的、来自血脉里的另一重影子。
喏,说到2026年属马的朋友,咱们就这么顺着虚岁的藤蔓,来摸摸瓜吧。若是2014年出生的木马小朋友,到那会儿,周岁12,虚岁13,正要迈入少年时光的门槛,人生第一个本命年,大概还懵懂着,烦恼的是功课和游戏。2002年的水马,周岁24,虚岁25,要么刚出社会,要么研究生毕业,站在世界的入口处张望,第一个本命年可能伴随着求职的焦虑或独立的兴奋。1990年的金马,周岁36,虚岁37,嗯,这叫“逢九”,俗话说“暗九”,也是道坎儿,事业家庭,压力正顶在肩头最吃劲的地方。1978年的土马,周岁48,虚岁49,这又是个“逢九”,眼看知天命,人生的下半场哨音隐隐可闻。1966年的火马,周岁60,虚岁61,花甲轮回,正式退休的年纪,感慨怕是比焦虑多了。再往上,1954年的木马,周岁72,虚岁73,已是古稀之后,看什么都多了一份云淡风轻。
你看,这么一排开,哪还是冷冰冰的数字?简直像一幅人生阶段的浮世绘。我总觉得,生肖这玩意儿,最妙的不是它预言了什么性格,而是它成了我们记忆里一个个小小的“时间锚点”。比如一说起“属马的”,我脑子里第一个跳出来的,不是“热情奔放”之类的词条,而是“哦,那大概是比我小两轮的人”,或者“跟我那表哥是一辈的”。这种定位法,粗糙,但异常亲切,像老书架上的分类标签,不是按学科,而是按“什么时候放上去的”来区分。
说起我表哥,他就是一匹78年的土马。2026年,正好48。我记得他36岁本命年那会儿,紧张得不得了。他是做建材生意的,那一年偏偏行业不景气,货款收不回,工人工资要发,急得嘴角起泡。舅妈从老家寄来一身红内衣红袜子,他嫌土,不肯穿,舅妈电话里气得直骂。后来不知是心理作用还是怎么,开车蹭了,虽然人没事,但把他吓够呛。第二天就乖乖把红袜子套上了,还自我解嘲说:“穿就穿吧,就当是给老太太个安慰赛。”结果那双袜子质量不咋地,下雨天走多了路,掉色,把他脚踝染红了一圈,晚上洗澡时发现,自己都乐了。你看,这就是我们这代人对待本命年的一种典型态度:将信将疑,但不敢全然不信,像是在人生的河岸边行走,宁可靠有红色标记的那一边,心里踏实点。
等到他48岁这年,也就是去年,我再见他,发现他淡定了许多。生意稳住了,孩子也上大学了。他反倒跟我聊起,这个本命年他想干点“出格”的事——不是做生意,而是报了个成人吉他班。我说你手指头跟钢筋似的,能按动弦吗?他哈哈一笑,说:“就是不为什么,就觉得这个‘轮回’走到一半多了,得给生活里添点不一样的声响。弹得好不好另说,就是听个响,告诉自己还能学新东西。”他这话让我琢磨了好久。或许,所谓“本命年”的焦虑,剥开那些玄乎的运势外壳,内核是对时间流逝的一种格外自觉的警醒。它像一个闹钟,每隔十二年就响一次,未必是催你躲避灾祸,也可能是提醒你:嘿,又一轮了,看看路上风景,想想接下去怎么走。
这就不得不提我的一位前同事老王,66年的火马。2026年他整六十。去年他提前办了退休,单位开了欢送会。会上大家让他讲两句,他端着酒杯,说了段我至今记得的话。他说:“我属马,今年59,虚岁叫‘逢九’,明年本命年,正式退休。都说这些是坎儿,我心里也嘀咕过。可回头看看,我这匹‘马’跑过的这几十年,哪一年是真正风平浪静的呢?坎儿一直都在,只是我们给某些年份贴上了特别的标签,好让自己在跨过去的时候,更有仪式感,或者,更小心一点。” 他最后说,他打算退休后和老伴儿换个方式“跑”——买辆房车,慢慢在国内转转,不走高速,专走省道、县道,看看那些以前匆匆路过却没停下来的风景。他把这叫做“给自己的退休本命年礼物”。你看,他从“躲坎儿”的心态,变成了“主动规划一个坎儿之后的风景”。这态度,我挺欣赏。
所以啊,当我看到现在年轻人过本命年,早已不像我们当年那样,带着些许惶恐和勉强。他们兴致勃勃地网购各种“本命年神器”:设计时髦的红手链、写着“鸿运当头”的潮袜、甚至还有印着卡通马图案的红内衣,把一种传统的“避忌”,过成了一种有趣的、有参与感的当代“仪式”。这没什么不好,文化嘛,本来就是流动的。用我女儿的话说:“爸,你们那套太沉重了,我们这就是图个好玩,讨个彩头,跟过生日吹蜡烛许愿一个性质。” 想想也是,一种古老的时间观念,能以这么轻松的方式延续下来,本身就是件挺有生命力的事。
话说回来,给小王算完年龄,他看着我列的那串数字,若有所思。我抿了口茶,茶已经温了,入口更显醇厚。我对他说:“岁数嘛,就是个数字。本命年呢,你要说它完全没道理,可千百年来这么多人念叨,总有它一点心理上的由头。你要说它多么灵验,那也未必。关键是你自己怎么看待这个‘坎儿’。把它当成一个反思的契机,一个调整步伐的借口,甚至只是一个给自己买件喜欢红衣的理由,都挺好。怕就怕,什么都没做,只是凭空焦虑了一年。”
他点点头,好像轻松了些,又问了句:“周老师,那您说,这十二生肖一轮一轮的,像什么?”
我望着窗外渐渐西斜的日头,想了片刻。我说,要我说啊,这不像一条直线跑道,而更像一条环形的、宽阔的漫步道。每隔十二年,你就经过一个挂着不同生肖标记的站牌。有的站牌提醒你“前面路滑,小心慢行”(比如本命年),有的站牌则写着“风景不错,稍作停留”。但路,始终是你自己在走。那站牌的意义,不在于预言你的跌倒或腾飞,而在于当你经过它时,会下意识地抬头看一眼,心里默念一句:“哦,又到这儿了。” 然后,整理一下行装,带着这一路积累的尘土与星光,继续往前走去。
小王走了,茶杯也见了底。我忽然想起,我自己虽然不是属马的,但每十二年,也总会遇到属马的亲友们进入他们的“特别年份”。看着他们,就像看着时间在不同生命轨道上,敲出的相似而又不同的节拍。这大概就是生肖轮回,留给我们最温情的一份礼物吧——它让我们在各自匆忙的线性人生里,找到了一个个可以共鸣的、循环的节点,然后相视一笑,说一句:“是啊,又到年头了。” 岁岁年年,就这么过去了,带着计算时的明晰,和感悟时的朦胧,都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