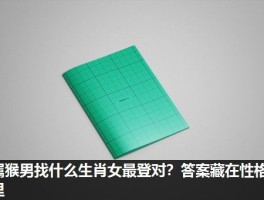那天在旧书摊翻一本泛黄的方言札记,看到“五方杂处”四个字,脑子里嗡地一下,倒不是因为它生僻,恰恰是因为它太活生生地映在眼前了。我想起小时候住过的那种大杂院,天南地北的口音在公用水龙头下交汇;更想起现在每日通勤的地铁,一车厢的人,低头看着不同内容的手机屏幕,仿佛一个个移动的、封闭的小世界,却又被物理空间紧紧地挤在一起——这不就是最现代的“五方杂处”么?四面八方来的人,带着各自的故事、习惯和目的,混杂一处,彼此擦肩,偶尔碰撞。
这个成语,说的就是一种高度混杂、流动、需要不断调试自身才能存续的状态。那要打一个生肖,哪个最能代言这种特质呢?我几乎没怎么犹豫,心里就跳出了一个答案:猴。
你可能会觉得,猴不就是机灵么?但“五方杂处”所要求的,远不止是机灵。它是一种更深层、更立体的“适应力”。在我看来,猴的适应力,简直像一种天赋的生存哲学。
首先,这种适应力是高度情境化的,近乎一种“社交变色龙”的本能。我认识一个属猴的朋友,老陈。他是做销售的,用他的话说,工作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词带点贬义,但他做起来却有一种令人叹服的真诚与自然。和学者聊天,他能接上两句冷门理论;和工人师傅蹲在路边吃盒饭,他能扯些家长里短、市井趣闻。他不是在“演”,而是能迅速捕捉到对方话语体系的频率,然后把自己的调子调过去,无缝接入。这就像山里的猴子,面对不同的群体——无论是自家猴群,还是路过的其他动物,甚至是观察它们的人类——都能迅速调整自己的行为和“沟通”方式,没有那种僵硬的“自我”需要时刻捍卫。在五方杂处的环境里,这种随时准备切换频道的能力,是润滑剂,更是通行证。
更深一层,猴的适应力带有强烈的学习和模仿色彩,一种“现实的学徒”心态。《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就是个极致例子,他那些通天本领,多少是“偷师”来的?从菩提祖师那儿学,从天庭的见闻里“偷”,甚至从一次次失败的战斗中学。猴子似乎天生不相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秩序或金科玉律,它们用眼睛看,用手脚试,用脑子琢磨,把外界的一切都当成可以拆解、模仿、乃至改进的素材。我记得有一次在动物园,看到一只猴子极其耐心地、反复地用草茎去钩游客掉落在隔离沟里的一顶帽子,那专注和尝试不同角度的样子,活像个沉浸在自己项目里的工程师。在快速变化、信息混杂的“五方杂处”之地,这种不固守成规、乐于从环境中直接汲取养分的能力,比任何僵化的知识都宝贵。
但说到这里,我心里又浮起一点疑虑,或者说,一种辩证的冷感。这种令人羡慕的适应力,它的背面是什么呢?会不会是根系的浮浅?我那朋友老陈,人缘极好,去哪儿都能混个脸熟,可有一次酒后,他也嘟囔过一句:“热闹都是他们的,我好像在哪都是个客人。”这话有点伤感。像猴子,固然能在山林、在边缘农田、甚至在城市的废墟里找到生存缝隙,但它们似乎很难像蚂蚁或蜜蜂那样,建立起一个深沉、稳固、代代相传的复杂王国。它们的智慧是点的闪耀,而非线的绵长。过分的适应,有时会不会稀释了某种“不顾一切”的执着和深刻?我欣赏猴的灵动,却也暗自警惕,怕自己在这眼花缭乱的世界里,也变成了一只永远在枝头跳跃、却忘了为何要出发的猴子。
话说回来,或许这正是“五方杂处”这个谜面给我们的现代启示吧。我们早已身处一个比任何历史时期都更“五方杂处”的时代,地理的边界在模糊,文化的碰撞成日常,信息的洪流从不止歇。像猴一样的适应力,不再是可选项,而近乎生存的必修课。它要求我们放下一些无谓的矜持,打开感官,敏捷地学习,在流动中寻找自己的锚点。但这种适应,不应该仅仅是随波逐流的漂移,或许,它更应该是一种主动的“游牧”——心中有方向,脚下无疆界。像水一样,遇方则方,遇圆则圆,但深知自己依旧是水。
所以,再想想“五方杂处打一生肖”,我依然觉得是猴。它不仅仅是一个关于聪明的答案,更像一个关于我们时代生存状态的隐喻。我们都在学习如何做一只现代社会的“猴子”,在混杂的枝桠间轻盈腾挪,同时,在心里默默守护着一小片属于自己的、安静的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