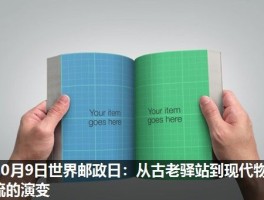《揭秘3月26日:道教杜炳爷诞辰与民间祭祀习俗》
农历三月二十六,这个日子在黄历上平平无奇。可你要是那天恰好在闽南的某个沿海村镇里,空气的味道都会不一样。海风的咸腥里,会混进一股浓得化不开的香火气,还有鞭炮炸开后的硫磺味儿,丝丝缕缕,钻进每条巷子。我最初注意到这个日子,是在泉州一座小庙的墙角碑文上,那石碑被岁月磨得厉害,“杜府元帅诞辰”几个字,得蹲下身,用手指慢慢描才认得全。坦白讲,那时候我心里犯嘀咕,杜炳?这名字在《道藏》里头,影子都淡得很,怎么在这儿,倒像是个了不得的大日子。
话说回来,我们这行跑久了就明白,经典里没有的,未必心里就没有。老百姓造神、供神,有一套自己的道理。杜炳爷,或者说杜王爷、杜府元帅,他的“履历”在民间说法里倒是挺丰滿。大抵是位唐代的武将,忠勇那种,后来似乎还兼通了医道,成了个能安境、能祛疫、能保平安的多面手。可你去看稍微正经点的地方府志,关于他,往往就那么干巴巴两三行,身份还时常打架。这种反差很有意思,官祀要的是秩序和典范,条条框框清楚;民祀呢,要的是灵验和亲切,最好是无所不能。所以一个在官方记录里面目模糊的将领,到了百姓口中,就成了能治小孩夜啼、能佑出海满舱、能镇一方邪祟的“自己人的神”。我记得在漳州一个村里,一位老阿婆跟我说得直白:“杜炳爷啊,就跟我们村里的老族长一样,什么事都能管,找他,踏实!”
踏实。这个词,大概就是关键。
我曾特意在三月二十六那天,跑到闽东一个以渔业为主的小村去看。那祭祀,真叫一个鲜活。庙不大,临着海,杜炳爷的神像被香火熏得黝黑,面容却雕琢得并不凶恶,反而有种朴拙的威严。供桌上,三牲五果是基本的,有意思的是旁边几样东西:一束新鲜的艾草和菖蒲,几包用黄纸裹着的本地草药根,最特别的,是几只小小的、用黑色纸张粗略扎成的小船。主祭的是村里最年长的老人,他的手布满老年斑,颤抖着把米酒洒在地上,嘴里念叨的不是什么成套的经文,而是断断续续的本地土白,我侧耳仔细听,大意是“元帅公今日好日子,喝杯酒,保庇咱出海的人眼前路亮堂,网网沉重,回港顺风……也保庇后生囝仔无病无灾,读书聪明。”没有华丽的词藻,全是具体而微的、关乎生计与健康的盼头。
周围聚着的村民,表情也放松,不像参加某些大典那样紧绷着。他们闲聊,说谁家去年今日许了愿,孩子的病果然好了;说去年台风来,村里几条船差点回不来,怕是元帅公暗中推了一把。这些话,你无法考证,但说话人眼里的光,是笃定的。那种笃定,不是源于对深奥教义的理解,而是源于一种代代相传的、近乎本能的信任。我递了支烟给庙门口歇脚的老庙祝,他咂巴着嘴跟我讲,潮汕那边也拜杜炳爷,但供品里黑色纸船就少见,他们更看重“五色豆”,大概是祛毒避瘟的意思。“隔一座山,话就不同;隔一道水,神办事的偏好也好像不一样咧。”他说完,自己先笑了起来。
这大概就是民间信仰的底子,它从来不是纯净水。你看这杜炳爷的祭祀里头,有道教神祇的科仪影子,有远古巫术用草药、纸船禳灾的痕迹,甚至还有那么点祖先崇拜的味道——把他当成一位有力的、仁慈的家族保护长者。老百姓其实不太在乎你属于哪个系统,他们进行的是一种“功能性”的选择与叠加。哪个神祇能在这个具体的、充满不确定性的生活领域(比如凶险的大海、比如孩童的健康)给我安慰和许诺,我就亲近他,为他过生日,跟他拉关系。杜炳爷,正是这种“社区全能型管家”角色的完美承载者。
所以你说,在现代,这仅仅是迷信吗?以我的经验看,事情没那么简单。没错,科学的解释早已覆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但科学能解答一切,却未必能安慰一切。那种对未知风险的恐惧,对社区共同体情感的归属需求,是需要一个寄托物的。杜炳爷的诞辰,在很多时候,已经演变成一个由头,一个让漂泊在外的游子想起归乡,让左邻右舍放下活计聚在一起,让古老的传说在老人对孙辈的讲述中再活一次的社区节日。它的核心,渐渐从对神力的无限祈求,部分转向了对人情与记忆的温热确认。我看见那些年轻的父母,也带着孩子来上香,他们未必真信孩子发烧是元帅公摸一下额头就能好的,但他们愿意让孩子知道,我们是这个村子里的人,我们和我们的父辈,都这样尊重我们的传统。这是一种文化的惯性,更是一种情感的锚定。
跑的地方越多,我反而越警惕那种高高在上的、“启蒙者”般的视角。民间信仰的力量,恰恰在于它的烟火气,它的不纯粹,甚至它的那点小小的“功利”。它像一株老榕树,根系深入地底,可能纠结着古老的、甚至不那么“正确”的养分,但它撑开了一片荫凉,让一代代人在下面聊天、祈福、找到自己的位置。杜炳爷,就是这样一棵地方性的“榕树”。
离开那个小渔村时,日头已经西斜。海面上金光粼粼,庙里的香火还未散尽。我忽然想起老阿婆那句“找他,踏实”。在变动不居的时代浪潮前,这份试图通过祭祀一位地方神祇而获取的“踏实感”,或许才是三月二十六日,最值得深思的余韵。城市里的宫观,神灵谱系森严;而乡野间的庙宇,供奉的往往是人们对“安稳”最直白的想象。这份想象,会随着渔船的柴油机声,随着下一代人走向远方而渐渐淡去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那个黄昏,空气里的香火味,闻起来依然具体而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