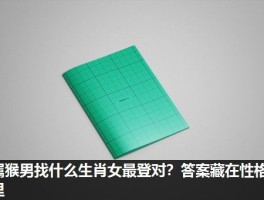我书桌的抽屉里,常年放着一本边缘起毛的笔记本。里面没什么系统性的研究,更多的是零散的观察:某位朋友对方案标点符号的偏执,母亲擦拭花瓶时那种近乎仪式感的专注,或者,我自己在提交一份报告前反复折腾格式的那股劲儿。这些碎片指向同一个模糊的影子——我们文化基因里,对“完美”那种爱恨交织的拉扯。它像一束光,吸引人靠近,可真的置身其中,那热度有时也灼人。
“尽善尽美”,这个词就这么自然地浮现在脑海里。它太端庄,太圆满,像一个悬在头顶的、晶莹却沉重的理想。后来才知道,这还是个谜面,打一生肖。若按常见的脑筋急转弯,或许会想到一丝不苟的牛,或精致灵巧的兔。但在我心里,那个答案几乎是不假思索的——是龙。不是因为它万能,而是因为它身上承载的那种“尽”,是一种别无选择的、命定的高度。
你看,“尽善”与“尽美”,拆开来看,要求的是两个向度的极致。先说“尽善”。善,在我们这里,远不止善良,更有“完善”、“至善”的意思,关乎德行与功用。龙是什么?是能幽能明,能细能巨,呼风唤雨,润泽苍生。它司水,掌管降雨,在农耕文明里,这便是至高的、关乎生存的“善行”。《易经》里那句“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描绘的是一种德行完备、位阶崇高的完美状态。龙的形象本身就是一部“尽善”的合订本:鹿角象征祥瑞长寿,牛耳代表任重聆听,鹰爪是果敢勇猛……它几乎集纳了所有被我们视为美好的品德与能力于一身,成为一种“至善”的图腾。这不是它选择的,是千百年的人文投射,硬生生将它铸就成了这样。
再说“尽美”。龙的美,不是小桥流水的柔美,而是一种糅合了力量、威严与神秘的综合美学。它的线条蜿蜒而充满张力,它的鳞甲闪烁着秩序与威仪的光泽。它是仅存在于想象与艺术中的造物,正因为脱离了具体生物的局限,反而获得了美学上绝对的自由,可以达到视觉与意念上纯粹的“尽美”。你在故宫的琉璃瓦上,在华表的雕柱间,看到那些腾跃的、庄严的龙,那种美是压倒性的,不容置喙的。它美得没有缺点,或者说,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完美”的定义。
但我总觉得,龙这种被赋予的“尽善尽美”,骨子里是透着孤独的。记得有次在博物馆,久久站在一件战国时期的龙形玉佩前。玉是温润的,可那条盘曲的龙,姿态里却有一种紧绷的、蓄势待发的紧张感。它必须完美,因为它不是凡物。这像极了生活中那些被寄予厚望,或被自己的心气所驱策的人。他们仿佛属“龙”,要求自己面面俱到,无可指摘。工作上要卓越,关系中要周全,形象要得体,内在要丰富。他们身上有光,让人钦佩,可那光的热源,常常是自我燃烧。那份“尽善尽美”的蓝图,稍有不慎,就会从理想坍缩成苛责的牢笼。所谓“高处不胜寒”,有时不是别人给的,是自己心里那条完美主义的龙,盘旋得太高了。
所以,猜这个谜,对我而言,更像一次自省。我们向往龙,是否也在无形中,将那套“尽善尽美”的尺码套在了自己身上?属不属龙,反倒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意识到,自己心里可能都住着一条对现状不满、想要腾飞又怕姿态不够漂亮的“小龙”。追求更好是本能,但“尽善尽美”或许本该是属神祇的,不属于有血有肉的人间。
我现在偶尔还会翻开那本笔记,看那些关于“完美”的片段。不同的是,我开始在旁边写下另一些东西:那个追求完美的朋友,学会说“这样也可以”时如释重负的笑容;母亲如今也会任由花瓶落一点灰,说“这样才有生活气”。我们依然欣赏龙的光芒,但或许,也该学着接纳蛇的蜿蜒、马的奔放,甚至猪的自在。生活这幅长卷,正因为有了这些“不完美”的笔触,才生动起来,才真正属于我们。
说到底,“尽善尽美”是龙,是一个灿烂的文化答案。而人生的答案,恐怕藏在那份对“完善”的追求与对“不完满”的接纳之间,那片广阔的、有风的真实地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