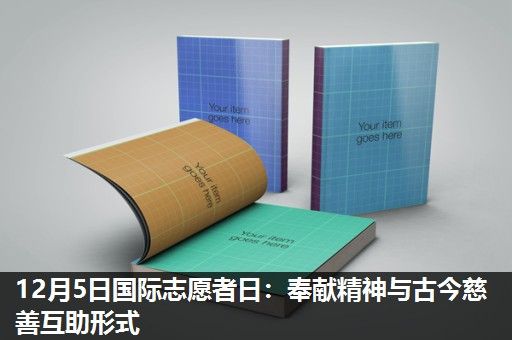整理旧物时,从一本快被压平的《存在与时间》里,滑出一张硬卡纸。我愣了好一会儿才认出它——十年前,某个偏远乡村小学暑期支教项目的志愿者证。照片上的自己,头发短得近乎板寸,冲着镜头笑得毫无保留,眼里有种现在想来颇为奢侈的、确信自己正在“改变些什么”的光芒。证件边缘已经泛黄卷曲,像一片被时间烘烤过的落叶。我把它搁在桌上,泡了杯茶,窗外的城市正沉入十二月初冬惯有的、灰蒙蒙的午后。大概是因为这个月份吧,思绪不由分说地飘向了那个几乎被仪式化了的日期:国际志愿者日。但我脑子里冒出的,全然不是鲜花、掌声或总结报告里的那些数字,而是一种更为复杂、甚至带着毛刺的体感。
以我的经验看,“奉献”这个词,被用得太过光滑了,光滑到失去了它原本应该有的、握在手里能感知到的纹理。我见过的奉献,很少是那种单向度的、喷射状的给予。更多的时候,它像一条浑浊的河,裹挟着疲惫、偶尔的自我感动、处理人际琐事时的烦躁,以及非常偶然的、如同河底金砂般一闪而过的真正连接的时刻。我记得第一次带队做社区老人关爱项目,我们几个大学生满腔热情,策划了文艺表演、健康讲座,忙得脚不沾地。结束时合影,老人们被我们簇拥在中间,对着镜头礼貌地笑。但散场后,我回头看见一位姓陈的奶奶,正慢慢地、有些吃力地把我们搬来的椅子一张张挪回原位。那个背影,像一根针,轻轻刺破了我心里那个充满成就感的肥皂泡。我们带来了热闹,留下了需要收拾的场地,然后我们离开了。那种“帮助”的体位,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有点居高临下?我们奉献了时间与热情,却可能未曾真正“看见”对方完整的生活。这让我后来对任何形式过于密集、如同“快闪”般的公益行动,都保持一份警惕。
说起这个,让我想到人类试图互助的那些古老原型。我偏爱研究地方志里那些琐碎的记载,比如明清时期江南一带普遍存在的“义庄”。那是一种宗族内部的自治保障系统,用族田的收入来赡养鳏寡孤独、资助子弟读书。它的逻辑核心是“血缘”与“地缘”,是一套熟人社会里的、带着明确责任边界的互助契约。还有西方工业革命时期工人自发组织的“互助会”,每月从微薄的薪水里扣出几个硬币,谁遭遇工伤、疾病,就从池子里得到一笔救急款。它的核心是“业缘”,是处境相似者抱团求存的理性计算。这些形式一点儿都不浪漫,甚至有些冰冷僵硬,但里面有一种沉甸甸的、持续的责任感。你知道你为谁负责,也知道谁能为你负责。它的网络不大,但编织得足够结实。
而我们现在呢?技术把网络的规模扩展到不可思议的地步。一次灾情,动动手指,善款可以瞬间汇聚;一个留守儿童的心愿,能通过社交媒体被千里之外的陌生人认领。这无疑是伟大的进步,高效、透明,打破了地域的壁垒。但话虽如此,可还有另一面。这种连接太“轻”了。轻点一次捐款按钮,和过去在义庄里目睹族中长辈分配粮米、在互助会里亲手将硬币交到工友遗孀手中,那份情感的重量和场景的记忆,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奉献的“成本感”在降低,这鼓励了更多人参与,但同时也可能让“奉献”本身,变成一种更纯粹的精神消费,或是个人情感账户上的一笔快捷存入。我接触过一些参与短期国际义工旅行的年轻人,坦白说,其中一部分人对于“项目地”的理解,可能还不及他们对旅行攻略里美食景点来得深入。他们奉献了金钱和时间,购买了一段“做好事”的体验和社交资本。这没什么好苛责的,人性本就复杂,利他心的起点千奇百怪。但作为从业者,我不得不思考,当奉献变得过于便捷乃至轻盈时,那种基于共同命运感的、扎实的责任共同体,该如何被建构和维系?
这大概就是最核心的那个难题了,古今皆然:如何越过“我们”帮助“他们”这道心理鸿沟,真正走向“我们”?我记得在云南一个山村,我们引进了一个不错的助学项目,但初期推进缓慢。直到我们放下项目书,跟着村里人一起,花了整整两周时间,用最原始的方式参与他们修一段被冲毁的村路。挖土、抬石,手上磨出水泡,一起蹲在工地上吃简单的午饭,听他们讲山洪来的那个晚上多么可怕。路修好的那天,什么也没说,但很多隔阂仿佛随着路通了也一起通了。后来那个助学项目,变成了“我们村里孩子上学的事”。那种体感,和坐在办公室里审阅受助学生名单,是截然不同的。身体力行的、共担艰辛的参与,似乎仍是融化隔阂最笨拙也最有效的一味药。
所以,回到手边这张安静的志愿者证。我感激那个夏天它带给我的、关于现实粗粝质感的启蒙,那远比任何理想主义的幻梦来得珍贵。现在的我,可能不会再拍那样一张笑容灿烂的照片了。我的反思变多了,行动也变得更审慎,有时甚至显得有些犹豫。但这不意味着热情的消退,或许恰恰相反,是因为我更加敬畏“帮助”这两个字所蕴含的沉重与复杂。国际志愿者日,在我看来,与其说是一个庆祝的节日,不如说是一个沉思的契机。沉思我们如何能在技术带来的高效与疏离之间,重新找到那种有温度的、负责任的连接;沉思在利他与利己之间,是否存在一片更开阔的、允许人性复杂性的灰色地带,让奉献不至于变成燃烧殆尽后的灰烬,而能成为一种可持续的、明亮而温暖的生活方式。
窗外的天色更暗了。我把那张旧卡片小心地夹回书里。赫尔曼·黑塞写过一句话,大概意思是,觉醒的人只有一项义务,那就是找到自我,并坚守自我。我想,在公益这条路上,或许也类似:找到那种能让你的内心踏实、也能让他人感受到尊重的奉献方式,然后,稳稳地走下去。尽管问题永远比答案多,但我猜,我依然会选择继续行走在这条路上,只是步伐和十年前,不太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