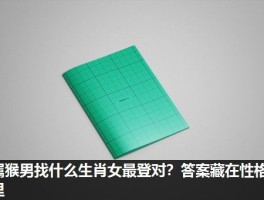《“劳苦功高”打一生肖?默默付出生肖代表》
午后,整理旧书,手指拂过一本蒙尘的成语词典。无意识地翻开,“劳苦功高”四个字就这么跳进眼里。愣了一会儿,脑子里浮现的倒不是什么宏大叙事,而是小时候镇上火车站外,那些等着扛活儿的“扁担”。他们蹲在墙角,影子缩成一团黑的,有人叫了,便默默起身,把上百斤的行李扛上肩,一步一步,压着青筋,挪上月台。完了,主家给几张零票,他们接过来,点点头,又退回墙角,等着。没人记得他们的脸。这大概就是“劳苦功高”这个词,在我心里烙下的最初意象——一种沉甸甸的、带着汗碱味的、却时常面目模糊的付出。
所以,当这个谜语摆在面前时,我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脑海里就站出了那个身影。牛。是的,就是它。
但我不想像教科书那样,仅仅说它象征勤劳。我总觉得,牛身上有种更复杂的、更让人心里发涩的东西。我老家村里就有这么一位,大家都叫他李伯。他一辈子伺弄着几亩水田,还有一头真正的水牛。春耕秋收,永远是起得最早、回得最晚的那个。话极少,你问他什么,他都是“唔”一声,点点头,或者摇摇头,眼神永远落在脚下的泥巴,或者手里的活计上。村里办红白喜事,需要出力气的笨重活儿,灶台边堆成山的碗碟,大家也总第一个想到他。他从不推辞,只是干。干完了,蹲在角落抽一袋烟,主家给塞包烟或一点吃食,他便接了,依旧没什么话。人人都说李伯是个好人,老实人,就像他养的那头牛。可“好人”与“老实”,在这年头,听上去总像带着一点点无可奈何的安慰意味。他的劳,他的苦,谁都看得见;可他的“功”呢?田里的收成是全家活命的根本,这自然是功;那些他默默帮衬过的邻里情分,也是功。但这些功,仿佛被日复一日的“劳苦”本身给稀释了,融进了背景里,成了理所当然的空气。你不去特意地想,就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这大概就是牛的处境。它的功劳,是地基式的。房子盖得漂亮,人们赞美琉璃瓦,赞美雕花窗,可有谁会特地蹲下来,拍拍地基说“你真了不起”?牛,以及像牛一样的人,他们的付出构建了某种基底,一种沉默的、承重的秩序。没有这秩序,一切光华都无从谈起。可他们的个体面目,却在这庞大的“基底”身份里,模糊了。有意思的是,我们赞颂牛,却也发明了“牛脾气”这个词,来形容那种倔强、认死理、不擅变通。这脾气从何而来?我有时觉得,那未必是天性,或许更是一种长年累月面对土地、面对沉默、面对一种近乎物理规则的重复劳作后,内化成的生命节奏。是一种对复杂外界交流的笨拙,也是一种对自身耕耘世界之方式的、固执的守护。不懂,也不想去懂那些虚头巴脑的,只管低头拉好我的犁——这何尝不是一种悲哀的尊严?
当然了,若论“劳苦功高”,马也是有力的候选。尤其在我们浩荡的历史叙事里,战马的形象何其光辉。它伴随英雄开疆拓土,它的功劳被写在史诗里,与将军的威名一同被传唱。这是一种被“看见”的、甚至被浪漫化的劳苦功高。它的嘶鸣是冲锋的号角,它的汗水闪着荣耀的金光。可我总觉得,那更多的是“马”作为一个辉煌意象的功劳。若具体到每一匹真实的、活过的马呢?它们同样要忍受饥渴、伤病、无休止的奔驰,同样会默默倒毙在陌生的荒野。它的“功”被宏大叙事吸收,而它的“苦”,却可能和那头耕田的牛一样具体而微。这让我想起那些历史剧里,镜头总是追逐着帝王将相,而无数小兵、民夫,他们只是模糊移动的背景。他们的劳苦,汇成了“功高”的浪潮,但浪花记不住任何一滴水。
想到这里,这谜语便不只是猜一个动物了。它像一根针,轻轻刺痛了我们文化肌理里某个习以为常的部分。我们向来推崇“默默奉献”、“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这诚然是美德,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带有宗教般牺牲色彩的美德。但推崇久了,是否也无形中形成了一种预期,一种道德压力?仿佛那些付出者,就必须、也只能是“默默”的。一旦他们开口言说自己的苦劳,一旦他们希求与功劳相匹配的认可或回报,就显得不那么“高尚”了。这对他者,是一种廉价的感动;对当事人,或许是一种沉重的绑架。
我记得有一次在职场,见过一个真正像老黄牛一样的技术骨干。项目最难的模块他扛,加班最多的是他,最后庆功宴上,发言领奖的却是八面玲珑的项目经理。大家拍着他的肩膀说“辛苦了,你是幕后英雄”。他笑笑,没说话。后来我私下问他,真的一点不在意吗?他沉默了很久,说:“活儿总得有人干。但有时候,‘英雄’这个词,听上去像块碑。”我当时心里一震。是的,颂扬有时是一种温柔的隔离,是把活生生的人,钉进一个光辉但冰冷的楷模框架里。比起遥远的颂扬,他们或许更需要一份切实的、对等价值的尊重,需要自己的付出被清晰“看见”,而非笼统地“感动”。
话说回来,若非要我在这个谜语里押一个答案,我心里那杆秤,还是微微倾向了牛。马,尤其是战马,它的劳苦与功劳之间,有故事,有传奇,有被叙述和记忆的通道。而牛,它的存在更接近一种本原的、哲学性的状态:付出即是存在的方式。它的功,深埋在生长的稻穗里,在安稳的炊烟里,在那些依靠这沉默基石才得以喧嚣的日常里。这是一种更彻底、也更孤独的“高”。
谜底揭晓与否,其实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当我们想到“劳苦功高”,我们脑海里浮现的那个形象,是金光闪闪的图腾,还是那个墙角沉默的、背着生活重负的侧影?我们是在消费一种感动,还是愿意去理解一种人生?
窗外的夕阳斜斜地照进来,尘埃在光柱里浮动。那个成语静静地躺在书页上。我想,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牛”与“马”,都有无数个李伯。他们构成了大地本身的厚度。而我们这些偶尔抬头看天的人,或许该做的,不仅仅是猜一个谜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