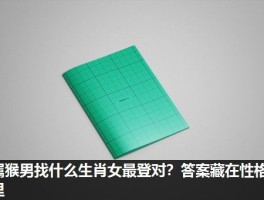话说那天整理旧书,碰落一本满是灰尘的民间谜语集。随手一翻,正好看到一行字:“无影无踪,猜一生肖。”心里咯噔一下,就愣在那儿了。这问题,好像小时候在夏夜乘凉时听老人提过一嘴,当时没答案,也就忘了。如今再看到,这四个字像钩子,一下子把我拽进了那种熟悉的、琢磨事儿的氛围里。泡上杯茶,对着窗外的暮色,我就忍不住想,这“无影无踪”,究竟是说谁呢?
字面看,是影子、踪迹都消失不见,形容彻底没了痕迹,走得干净。引申开来,是神秘,是迅捷,是那种在你意识到之前就已经完成了一切、悄然退场的能力。这么一想,生肖园子里,有几个家伙的身影,就在我脑子里晃悠起来了。
第一个蹦出来的,是鼠。这几乎是下意识的。我小时候在乡下老屋住过,那种砖木结构的老房子,是老鼠的天下。记得有一次深夜点着煤油灯看书,眼角瞥见一个灰影沿着墙根“嗖”地一下过去,再定睛看,什么都没有了。不是它跑远了,而是它钻进了某个我根本不知道的、墙与地板的缝隙里。那种消失,不是撤退,更像是融入了环境本身,仿佛它本就是阴影的一部分,此刻只是回到了阴影之中。它的迅捷,不在于直线奔跑多快,而在于对复杂地形和隐秘通道的掌控,在于那种瞬间的“隐遁”。古人说它“胆小如鼠”,这“胆小”或许正是它生存的智慧——不留下对抗的痕迹,只留下消失的背影。这么看,“无影无踪”给它,好像挺贴切。它是一种现实的、充满生存谋略的“消失”。
但脑子里另一个声音说,且慢。论神秘,论那种悄无声息、了无痕迹的移动,蛇岂不是更胜一筹?我记起有一年爬山,在枯叶覆盖的山径上,差点一脚踩上一条盘着的乌梢蛇。它静止时,花纹和枯叶几乎一体,毫无破绽;受惊而动时,不是“哗啦”一声,而是贴着地面,一种流畅到诡异的、丝滑的扭动,嗖地就滑进了旁边的石缝,连落叶都没怎么惊动。那过程,真的堪称“无影无踪”——你甚至看不清它是怎么启动、怎么变向的。蛇在文化里,也常和幽深、隐秘、甚至带着点神异色彩的事物联系在一起。它的“无影无踪”,带着一种静谧的、冷血动物的优雅和突然性,和鼠那种慌慌张张的钻营感不太一样。它更像一个光影里的忍者。
这么一比,就有意思了。为什么我们很少用“无影无踪”去形容同样以速度见长的马呢?马跑起来,蹄声如雷,尘土飞扬,那是阳刚的、充满存在感和痕迹的奔驰。猴呢?上蹿下跳,吱吱喳喳,留下的是折断的树枝和喧闹的回声。它们的“快”,是张扬的,是留下强烈印象的。而鼠和蛇的“快”,终点是“消失”,目的是“抹除痕迹”。这似乎关涉到一种更深层的特质:对自身存在感的管理。一种是有意无意地彰显“我来了”,另一种是本能地追求“仿佛我没来过”。这不仅仅是习性的差异,几乎像是一种处世哲学的隐喻了。
想着想着,我甚至想到了那个并不存在于现实世界的生肖——龙。它倒是真正符合“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描述,腾云驾雾,能隐能显,这才是终极的“无影无踪”吧。但这答案太“偷懒”,也太脱离我们日常所能观察和体会的那种“消失”了。民间谜语,根子还是扎在泥土里、墙角边的生活观察。
绕了这么大一圈,我倾向于哪个答案呢?说实话,我有点两难。从我个人更鲜明的生活体验和瞬间的直觉冲击来说,我或许稍稍偏向于蛇。那次山径上的遭遇,那种冰冷的、丝滑的、瞬间融入环境的消失,给我的震撼更持久。鼠的消失,我见惯了,甚至带点厌烦;而蛇的消失,让我愣在原地,心里生出一种对自然造物的微妙敬畏。它更贴近“神秘”二字。
但话又说回来,谜语是民间的智慧,它服务的对象是千百年来与鼠患更普遍斗争、对鼠的行踪更为熟悉的农人与市井百姓。对他们而言,一眨眼就找不到、怎么堵也堵不完的“家贼”,或许才是“无影无踪”最生动、最接地气的注解。
这么一想,最终指向哪个生肖,似乎又不那么要紧了。这个琢磨的过程,反而让我品出些别的滋味。我们人呐,总是喜欢用动物的特性,来镜子一样照见自己性格的某些幽暗角落。我们说一个人“滑得像条泥鳅”、“躲得无影无踪”,这里面有贬义,形容其狡黠、不负责任;但有时,或许也藏着一丝无奈的羡慕,羡慕那种能在复杂境遇里全身而退、不落痕迹的“精明”或“低调”。那种“无影无踪”,何尝不是一种在纷扰世间自我保护、或是积蓄力量的姿态呢?
茶喝完了,夜色也浓了。那本谜语书,我又放了回去,灰尘都没掸干净。有没有标准答案,对我而言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四个字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对“存在”与“痕迹”的一点胡思乱想。做一个轰轰烈烈、留下深深辙印的人,还是做一个审时度势、懂得适时“隐身”的人?这问题太大,没有答案。但看着窗外沉沉的夜,我忽然觉得,能像鼠或蛇那样,在必要的时刻拥有一种“无影无踪”的选择权,或许,也是一种了不起的天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