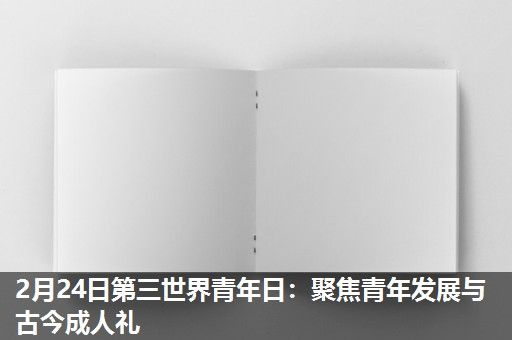我记得那是在缅甸掸邦高原的一个小村庄,二月末的阳光已经带着锋利的灼热。村口褪色的公告板上,一张用蓝色圆珠笔仔细描过的标语,在热风里微微卷着边——“纪念第三世界青年日”。字迹很认真,却和旁边漫不经心的涂鸦、早已过期的农药广告挤在一起,有种奇特的、被搁置的孤寂。不远处,几个年轻人正赤脚把晒干的辣椒收进麻袋,扬起的红色粉尘粘在他们汗湿的额发和肩膀上。那个“青年日”的标语,像一句来自遥远他乡的、口音陌生的问候,飘荡在他们沉重而具体的劳作之上。
这景象让我怔了好一会儿。这么多年,从东非的裂谷城市到东南亚的雨林村落,我参与过、也旁观过许多以“青年发展”为名的项目。我们带来课程、小额贷款、创业比赛,画着上升箭头的逻辑框架图。我们说,发展意味着机会,意味着赋能,意味着通向现代性的光明大道。直到你蹲下来,和那个叫朱马的青年一起,看他用从报废摩托车上拆下的零件,加上几块捡来的太阳能板碎料,试图攒出一个能给手机充电的装置时,你才会触碰另一种坚硬的真实。他的手很粗糙,被金属划出不少口子,但眼神里有种极度的专注。他没什么“机会”,但他必须创造。那一刻我忽然觉得,在资源如此赤裸匮乏的地方,所谓“发展”,对许多青年而言,或许根本不是线性的向上攀登,而是一种在逼仄缝隙中学习“无中生有”的生存技艺——一种匮乏中的创造。这创造可能微不足道,可能最终失败,但它关乎尊严,关乎一种不肯完全躺平的挣扎。朱马想要的,或许不是我们项目书上的“成为企业家”,而仅仅是让家人晚上有光,能联系上在外省打零工的父亲。他的“发展”,刻度如此微小,又如此千斤沉重。
这让我想起了“成人礼”这件事。以前在埃塞俄比亚南部,我接触过一个社群,那里的青年要经历一系列严酷的身体考验与隔离仪式,才被承认为男人。长者会用特定的荆棘在皮肤上留下疤痕,那过程无疑是痛苦的,但痛苦被赋予了清晰无比的意义:你通过了,你就不再是孩子,你拥有了新的权利与责任。整个社群见证、并确认了这种转换。
可今天,在朱马们生活的世界里,那种集体的、仪式性的“成人礼”正在消逝,或者早已名存实亡。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沉默的、不被庆祝甚至不被看见的“隐形成人礼”。它可能是终于攒够钱,登上前往海湾国家打工的航班,在机舱关闭灯光后,独自吞咽下的那一口恐惧;可能是拿到第一份为期三个月、没有任何保障的纺织厂合同,指缝里从此洗不净的染料气味;可能是在父母病倒后,十六岁的你自然然地扛起锄头,成为户主,去和村干部低声下气申请救济的那个下午。这些时刻,同样充满撕裂的痛楚,同样标志着一个天真的终结,但它们发生得悄无声息。没有祝福的歌舞,没有长者的训诫,没有象征新身份的信物。社会没有为这些创伤性的过渡提供任何“意义”的框架,它们只是被默认为生存的必然代价。于是,成长变成一场漫长的、不被承认的内伤。
我有时会觉得,我们这些所谓做青年工作的人,是不是太执着于输送“工具”——教你编程,教你记账,教你演讲——却太少去关注如何为他们正在经历的、这些沉默的“成人礼”进行精神上的接生?我们是否应该,哪怕只是偶尔地,提供一个类似“仪式”的空间,去承认那份疼痛的合法性,去帮助他们把那被迫的早熟、那生存压出的褶皱,整合进自我叙事里,而不是当作需要掩盖的耻辱或创伤?
曾有一次不成熟的尝试。在一个城市边缘的青年中心,我们没搞领导力培训,只是组织了一次“故事之夜”,主题是“我成为大人的那个瞬间”。起初很冷场,直到一个总是沉默的男孩,说起他第一次在建筑工地领到工资,全部汇回家后,自己躲在工棚吃白饭配盐巴,不是因为穷到那份上,而是“想尝尝父亲过去十年每天吃的滋味”。他说,咽下那口咸涩的饭时,他觉得自己童年的味觉永远结束了。他说完,房间里是长久的安静,没有掌声,但有一种更厚重的东西在流动。那晚,没有解决任何“技能”或“机会”问题,但我感觉到,某种看不见的、紧绷的东西,在几个年轻人身上微微松动了。那像是一次微小的、迟来的“仪式性见证”。或许,有效的支持,一部分应该是这种“见证”——做他们隐形伤口的第一个,也是温和的确认者:“是的,那很痛。是的,那改变了你。我看到了。”
这很难。系统性的困境如同巨石,我们提供的,最多不过是一小片树荫,或一瓶水。我也有很多无力的时刻,怀疑自己是否只是用另一种方式,将他们的苦难“浪漫化”或“理论化”。
离开那个掸邦村庄前,我又见到了朱马。他的充电装置居然勉强成功了,闪着不稳定但确实存在的光。他有点得意,给我看时,忽然问了一句没头没尾的话,用的是生硬的英语,可能从哪个过路游客那儿学来的:“老师,你们总说‘未来’。我们的‘现在’,是不是就是你们过去的‘未来’?”
我答不上来。车扬起红色的尘土,后视镜里,那个“第三世界青年日”的标语越来越小,最终和村庄、山峦融为一体。朱马的问题,和他手中那簇微弱的光,却一直跟着我。我们设定一个日子来谈论他们,仿佛他们是一个需要被周期性记起的议题。而他们,则在每一个没有被命名的、普通或艰难的日子里,进行着自己无声的成年。或许,真正的纪念,不是在这一天说出多少宏大的词,而是能否在那无数个沉默的“成人瞬间”里,更谦卑一些,学着去看见,甚至,只是学会不去打扰那种充满痛苦的、坚韧的生成。
瓦妮莎,那个在内罗毕贫民窟教孩子们用废弃塑料做雕塑的姑娘,曾对我说过一句我总也忘不掉的话。她说:“我们这里,大人总告诉孩子,要逃离这里,去看大海。可如果,你从未学会如何与脚下的泥土相处,就算看到了海,你又真的能认出它吗?”
嗯,这是一个好问题。你曾见过真正的海吗?那和我们沙地上的画,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