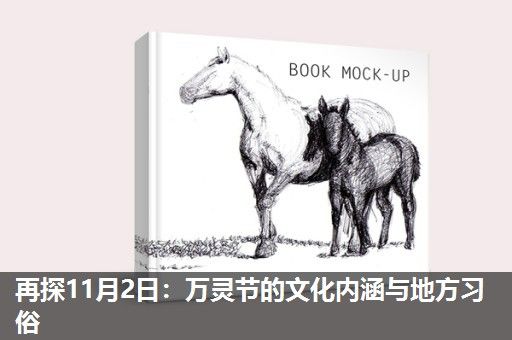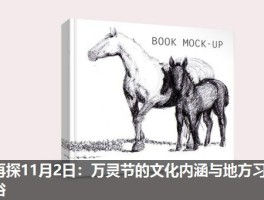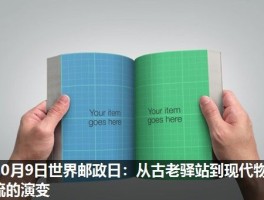再探万灵节
那气味,我总也忘不了——烛火将尽时升起的微呛,混合着亚平宁半岛深秋夜雨打在古老石阶上的湿漉,还有,一种奇异的甜,来自褪色缎带与快要萎谢的菊花。那是许多年前,我在托斯卡纳山区一个名叫圣吉米尼亚诺的小镇墓园里,第一次真正“遇见”万灵节。那时我年轻,带着笔记本和一种天真的猎奇心态,以为自己是来“记录”一种异域风情。我记得自己详细记下了墓碑前蜡烛的数目、鲜花的种类,甚至试图分辨祈祷词的音调。我以为我懂了。直到这些年,在拉美的烈日下、在另一些潮湿的墓园里回过味来,我才明白,那时的我,不过是站在仪式门口的观光客。所谓“再探”,并非旧地重游,而是岁月与更多的远方,在你心里埋下了另一些种子,迫使你回头,重新打量那个你以为早已归档的节日。
万灵节,在许多中文语境里,常被笼统地归入“缅怀先人”的范畴。但只要你把脚步挪动一下,从意大利静谧的教堂墓园,走到墨西哥瓦哈卡灯火通煌的街头,你就会立刻嗅到生死观那截然不同的“在地性”。在圣吉米尼亚诺那晚,仪式是内敛的,甚至是沉默的。一家一户,默默擦拭亲人的墓碑,摆放好白菊,点燃长明烛。夜色四合,整个墓园变成一片颤动的、温暖的光之海,但寂静无声,只有雨滴和呼吸。那是一种内向的凝聚,生者与逝者在一个被烛光划出的神圣空间里,进行一年一度的、庄重的“家庭团聚”。死者是安息的,是需要被小心呵护的记忆。
而后来,我在墨西哥米却肯州的湖滨小镇哈尼齐奥,经历了另一个万灵节。这里的死亡不是白色的、静谧的。它是金色的万寿菊铺就的引路桥,是色彩绚烂到近乎狂欢的骷髅糖,是坟墓边彻夜响起的马里亚奇音乐,是满溢着龙舌兰酒与莫莱酱香气的盛大餐宴。人们谈论逝者,如同他们还在席间,会为一句俏皮话发笑。我曾疑惑,这欢乐是否冲淡了哀思?直到我与一位本地老人多纳·卡尔门交谈,她正为早夭的儿子摆上他最爱玩的旧陀螺和一包已停产多年的辣味糖果。她眼神明亮,没有泪,只有一种滔滔不绝的讲述欲。“他喜欢这个,”她抚摸着陀螺,“要是他今天回来,看到这个,准会得意。”那一刻我触电般领悟:在这里,死亡并非隔绝,而是一次状态转换。万灵节不是生者单向的缅怀,而是一个双向的、欢庆的“重逢日”。逝者是要被热闹与生趣“请”回来的,他们依然是这个情感共同体里鲜活的一员。一个内向的守夜,一个外向的欢宴,背后是两种与死亡相处的哲学:一边是“慎终追远”的静默抚慰,另一边是“生死共存”的喧闹宣言。
于是,我学会了不再仅仅观看仪式,而是去凝视那些仪式中的“缝隙”,那里往往藏着记忆最真实的质地。我记得在墨西哥城一个庞大的公共墓园里,看到一个老妇人,她不厌其烦地擦拭着三块并列的、没有姓氏的墓碑。她的动作轻柔得像在抚摸婴儿的脸颊。后来我得知,那是她的丈夫和两个儿子,死于一场无从追究的车祸,官方记录潦草,只剩编号。她没有华丽的祭坛,只有三块干净的石头和一束从市场最便宜角落买来的向日葵。那是一种何等固执的、对抗行政性遗忘的努力——用最微小的肉身劳碌,去对抗一个巨大而冰冷的编号系统。记忆,在这里,首先是一种政治,然后才是一种情感。
当然,变化无处不在,这也是“再探”时无法回避的沉郁视角。回到意大利,我发现一些小镇的墓园,祭品越来越精致,却也越来越“标准化”——从超市购买的统一包装的鲜花、工业化生产的纪念牌。年轻一代匆匆而来,放下物品,刷一会儿手机,又匆匆离去。仪式还在,但那种全身心沉浸的、与社区共在的“场”正在消散。我感到惋惜吗?是的,有一点。但我又警惕自己,不要陷入那种怀旧的、本质主义的乡愁。或许,那种庄重的静默,本就与一个高度原子化、流动的现代社会格格不入了。商业化的侵蚀,有时也是传统在新的社会结构下,一种笨拙的、变了形的延续。它流于形式,恰是因为它赖以生根的“共同体”土壤已然稀薄。这无关对错,只是一个文化评论者必须正视的、略带凉意的现实。
话说回来,驱使我不断“再探”的,终究是那些无法被标准化、无法被商业化的时刻。在危地马拉高原的圣地亚哥-阿蒂特兰,玛雅文化与天主教达成了某种深沉的融合。那里的万灵节,家庭祭坛的核心不是圣人像,而是一筐经过精心挑选的、形状各异的玉米、豆子和南瓜——这是玛雅世界观里生命的根本。祭奠先人,即是感恩并维系这片土地的丰饶,逝者是回归大地、滋养新生的循环之力。这让我悚然一惊:我们纪念的,或许从来不只是“逝去的他们”,更是“赖以存续的我们”。仪式是一种咒语,反复吟诵着生者与土地、与血脉、与时间的古老契约。
绕了这么远,我想说的是,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的记忆被云端存储,我们的社交身份在死后可能以“纪念账号”的形式尴尬存续——万灵节这类实体性仪式,反而散发出一种近乎悲壮的珍贵。它笨拙、麻烦、需要你亲身前往,需要你沾染尘土与烛泪。它无法一键转发,无法被量化点赞。但也正因如此,它成为了一种抵抗,抵抗记忆的扁平化与数字化消解。当我们亲手擦拭一块墓碑,当我们为逝者摆放一碟他生前嗜好却已不时髦的点心,我们完成的,是一次充满体温的“再创造”。我们不是在调用一段数据,而是在用自己的感官、劳作与当下的情感,去重新编织与逝者的联系。这联系脆弱如风中之烛,却也因此,具有了数字记忆无法比拟的生命痛感与情感重量。
所以,万灵节最终叩问的,或许是未来的我们:当我们这代人故去,我们留给后人的,是一串可以随时被清空或破解的密码,还是一座需要他们亲自弯腰、动手清扫的坟墓?是云端一片整洁但虚无的“数字陵园”,还是容许他们摆放上一包辣味糖果、一个旧陀螺的实体空间?我们渴望的纪念,是便捷的访问,还是一次次麻烦的、却充满具体温度的“再探”?
雨夜墓园的气味,或许终将飘散。但那份在湿冷空气中,固执地为逝者点亮一盏烛火的心意,那份在数码洪流里,逆流而行的、古老的思念姿势,我希望它能以某种方式,继续流传下去。哪怕,只是以最微弱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