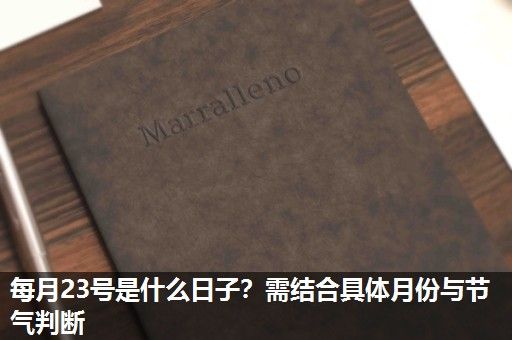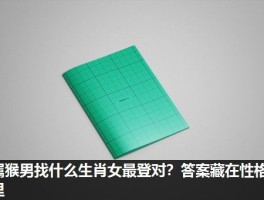《每月二十三号》
翻旧笔记本,忽然看到一行没头没尾的记录:“二月二十三,黄昏,灰蓝与粉紫的交界,风是潮的。” 我愣了一会儿,才想起那是好几年前,在南方老家,春节早已过完,但寒意又杀了个回马枪的那几天。就是那个傍晚,我出门散步,走到河堤上,暮色正以一种迟疑的速度沉降。天空不是纯粹的暗,而是一种浑浊的、将雨未雨的灰蓝,靠近西边山脊的地方,却又透出些疲乏的粉紫。风从河面吹来,不冷,但带着一股明显的、润润的潮气,扑在脸上,像一块半干的毛巾。就是那一刻,我莫名地看了一眼手机——二月二十三号。一个毫无特殊性的公历日期。可那种空气的质感,天光的色调,还有心里那股春节热闹散尽后、新一年又尚未真正舒展的悬空感,却如此具体。我当时就想,这个二十三号,和六月的二十三号,肯定不是同一个日子。它的意义,大概是被它所处的这个时辰——二月,早春,准确说,是雨水节气末尾——给浸染透了的。
从那以后,我便开始不自觉地留意每个月的二十三号。当然不是有什么纪念,而是像在验证一个模糊的猜想:日子本身是空白的画布,真正往上涂抹色彩的,是它背后那个正在行进中的节气。所谓节气,哪里只是黄历上的几个字,它是光线倾斜的角度,是空气的密度,是植物呼吸的节奏,也是人身体里某种难以言明的韵律。
就拿二月二十三来说吧。它常常卡在“雨水”的尾巴上,偶尔已经一脚踏进了“惊蛰”的门槛。在我们那儿,这个时节最明显的,是一种“催促”与“等待”的矛盾。泥土已经酥软了,蚯蚓开始翻动,迎春花零零星星地开,但那点鹅黄在庞大的、尚未退净的灰褐色背景里,显得有点怯生生的。你会觉得整个自然都在暗中用力,在积聚,但那层最后的、看不见的薄壳还没被顶破。风里的潮,就是那种积聚的呼吸。我记得有一年二月二十三,父亲在电话里说,田埂上的草籽已经绿了一层绒,但还不能放水,得再等等,等“惊蛰雷”在云里闷响了,那才是真的号令。你看,这个日子的意义,就在于它是漫长冬季与真正春季之间,那段最暧昧、最心痒的过渡。它不是起点,也不是高潮,它是屏住呼吸的那一小会儿。
而到了五月二十三号,整个世界的情绪就全变了。这时候,“小满”刚过不久,“芒种”迫在眉睫。小满,这个词多妙,是那种将满未满的丰盈感。五月下旬的南方,阳光已经有了重量,但不是七八月那种砸下来的酷热,是醇厚的、金晃晃的,照在开始灌浆的麦穗上,能看出一层毛茸茸的光晕。空气里充满了植物汁液饱满的、微甜的气息,混合着泥土被晒暖的腥香。二十三号前后,我总觉得空气里的“野心”最膨胀。一切都铆足了劲,麦子想变黄,瓜藤想疯长,连午后远处传来的拖拉机的嗡嗡声,都带着一种勤勉而急迫的节奏。这是一个盛大宴席的筹备期,你能听到厨房里锅碗瓢盆热闹的声响,闻到各种食材下锅的香味,但宴席本身还未开席。身处这样的日子,人会莫名地也跟着躁动起来,觉得该做点什么,该完成点什么,好像不然就辜负了这一片蓬蓬勃勃的生长力。这个二十三号的意义,是鼓胀,是临界的饱满,是箭在弦上之前,那最沉静又最紧张的一瞬。
八月的二十三号,又是另一番光景。节气多半在“处暑”附近。“处”是“止”,暑气至此将止未止。这时候的炎热,与七月的暴烈不同,它开始有了破绽。比如,清晨五六点,你推开窗,会猛地吸到一口清冽如泉的空气,那是夜晚偷偷酿造的凉意。但到了中午,太阳依旧毒辣,只是那光线里,不知不觉掺进了一点金属的、白晃晃的质感,不像盛夏那般浑厚了。最明显是黄昏,落日的时间明显提前了,霞光不再是一片灼热的红,而常常是淡淡的、水彩似的紫与金。我记得去年八月二十三号傍晚,我坐在小区长椅上,忽然一阵风吹过,卷起几片早凋的梧桐叶,沙沙地响。那声音干燥、清脆,带着明确的秋天消息。我心里咯噔一下,哦,狂欢要结束了。八月的二十三号,就像一个乐章的转折点,从盛夏最激昂、最绵长的部分,开始转向一段舒缓的、带着凉意的间奏。它的意义,在于那最初的、几乎难以察觉的松动与裂缝,是盛大之后,第一声微弱的叹息。
这么数下来,十一月的二十三号,就几乎是冬天的信使了。“小雪”节气前后。白天变得很薄,阳光苍白无力,下午四点多就开始收拢。风是干的,尖的,带着哨音。树叶几乎落尽,剩下光秃秃的枝桠,线条利落地分割着天空。这时候的自然界,是一种坦诚的、甚至有些肃杀的简洁。它不再生长,而是在收藏,在收缩,在向内沉淀。这个日子的意义,是一种清空和预备。我记得有年十一月二十三号,我赶一篇稿子到深夜,起身关窗时,发现夜空是一种沉静的、天鹅绒般的深蓝,星星清冷地钉在上面,格外清晰。那一瞬间,白天的所有烦乱好像都被这巨大的、寒冷的寂静吸收掉了。这个二十三号不给你任何蓬勃的许诺,它只给你一片干净的、可供沉思的留白。
所以你看,每月二十三号是什么日子?它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它不是节气本身,却总是徘徊在某个节气影响力的峰谷之间。它像一个固定的观察哨,让我在飞逝的时间河流中,找到一个可以暂时泊岸的标点,去体会当下那一刻,天地正在上演的是哪一出戏码。节气是宏大的乐章结构,而每一个普通的、被我们忽略的日期,比如二十三号,就是乐章里那些承上启下的小节,有它自己的和声与表情。
话说回来,这种对日期的敏感,或许也是一种对抗遗忘的方式吧。用天空的颜色、风的触感、空气的味道,去给抽象的时间打上锚点。当我想起某年的五月二十三号,我首先想起的不是做了什么,而是那股麦浆般甜腥的、充满野心的空气。时间就这样,从数字变成了可以触摸的肌理。
又快到下个月的二十三号了。会是哪一出呢?我竟然有了一点小小的、无关紧要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