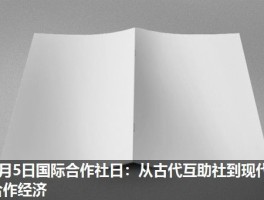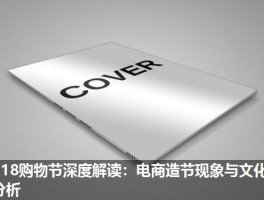《农历六月十九观音菩萨成道日:民间祈福习俗探源》
记忆里的那股气味最先醒来。是江南梅雨季末尾,凌晨四点的空气,沉甸甸地饱含着水汽,又被人间香火硬生生煨暖了、熏透了。栀子花将败未败的甜腻,混着寺院墙根青苔的腥凉,再被一股宏大、执着、不容分说的线香味一统天下——那是无数炷香在青铜香炉里集体燃烧的味道,辛辣,温暖,有点儿呛人,却又奇异地让人心安。外祖母粗糙而潮湿的手紧攥着我的手腕,她的蓝布衫后背上,有一小块被汗水濡湿的深色痕迹,在朦胧的天光里像一枚安静的印记。我们挤在石板路上,前后左右都是细碎的脚步声、压低的咳嗽声、念珠相碰的轻响,汇成一条沉默而湍急的河流,流向山门上那一片晕开的、橘红色的灯火。
我那时太小,只觉得困,脚趾在湿透的布鞋里不安地蜷缩。成道日?观音菩萨为什么要“成道”?她不是一直都坐在莲花上,微笑着看我们吗?这浩浩荡荡的人,起这么大早,挤得浑身是汗,究竟在求什么?是为了抢那传说中的“头香”,让愿望能第一个被听见吗?我看见身边一位老妇人,几乎是被后边的人推着走,她脸上没有急切,反而是一种近乎木然的平静,嘴唇极轻微地嚅动着,反复念叨同一句什么。那一刻我模糊地觉得,大家奔赴的,或许不只是神佛的殿前,更是奔赴一场自己与自己约定的、郑重的仪式。这仪式感,比那缕青烟飘到菩萨眼前的物理速度,更要紧。
话说回来,为什么是农历六月十九?这日子既非播种,也非收割的节点,在节气表上显得有点突兀。后来我听过好些说法。有附会传说的,自然是讲妙善公主于这天证道。但我更倾向于另一种,听起来没那么“神话”,却更接地气的解释:这与江南的农事节奏和气候,恐怕脱不了干系。阴历六月,长江中下游的“梅雨”往往刚过,转入伏旱,正是早稻收割、晚稻插秧的间隙,一场关乎下半年收成的酷暑正要拉开序幕。此时,台风、干旱、虫害,种种不确定性悬在头顶。农人难得有了一点喘息的空当,便将心中对自然之力的敬畏、对未来的忐忑,寄托于这位闻声救苦的菩萨。选择一个相对农闲的日子,举行一场集体的祈福,既是对上半年劳作的慰藉,更是对下半年光景的祈请。信仰的根,到底还是扎在泥土与生计里。或者说,菩萨的“成道”,在民间语境里,或许悄悄演变成了一个“节点”,一个让凡人可以理直气壮地停下脚步,整理惶惑,再重新上路的心理藉口。
于是,放生便成了这一天最耀眼,也最让我心情复杂的仪式。我见过湖边、河边热闹的场景:水桶里挤挨着的泥鳅、鲤鱼,甚至还有从市场匆匆买来的田鸡。人们口中诵着佛号,小心翼翼地将它们倾入水中,看着它们倏忽游走,脸上便荡开一种如释重负的、满足的笑意。起初,我也简单地将此理解为一种功德的“交易”——以物质的付出,换取神佛的福报积分。可后来,有一件小事触动了我。
有一年六月十九,在浙东一个村子,我看见一位阿婆独自在村口的小溪边放生。她放的是几条很小的鲫鱼,用一个旧铝盆装着。倒鱼之前,她对着盆子低声絮叨了好一会儿,像在叮嘱什么。完后,她并不立刻离开,而是蹲在石埠头上,望着溪水出神,目光跟着那几尾鱼游动的方向,直到它们完全消失在菖蒲丛的阴影里。那神情里,有一种近乎温柔的牵挂。我忽然觉得,对她而言,这或许不止是“放”,更是一种“还”。是将从自然中索取(或目睹他人索取)的生命力,以一种郑重的方式“还”回去。这是一种极为朴素的宇宙观:我与这些生灵,与承载它们的河水,乃是一体的。我的“生”与它们的“生”,在某个层面上紧密相连。通过这个动作,她不仅在为自身积福,更是在修复一种想象中的、和谐的生命关系秩序。这种心理动因,远比冰冷的功德计算要温热,也厚重得多。它源于古老的共生记忆,只是借用了佛教放生的形式来表达。
扯远了,再回到菩萨本身。我时常觉得,观音,尤其是那位逐渐定型的、中年女性形象的观音,能在中国民间获得如此无远弗届的崇拜,实在是一场极其成功的“本土化”。一个剔除了恐怖威仪,面容圆润慈和,仿佛邻家那位最有智慧、最富同情心的婶母或祖母的神祇,她倾听的姿势永远微微前倾。民间传说里,她总能幻化成各种身份——渔妇、村姑、老妪——直接介入最琐碎的苦难。这极大地消解了神与人之间的隔阂。我观察过,女性信众在观音像前的私语,往往最为细密、绵长。她们求子嗣、求安康、求丈夫顺利、求儿女成才,诉说的尽是些烟火人间最具体的困顿。这让我形成一个或许有些个人的看法:民间信仰中观音菩萨的核心魅力,恰恰不在于那些精深的般若智慧,而在于其超凡的“响应性”。老百姓不太关心“真如”、“空性”,他们需要一个能听懂灶台边叹息、病榻旁呜咽,并且愿意“管一管”的神。观音,就是这样一位“管事”的、母亲般的神。她的殿堂,不像哲学讲堂,更像一个永远亮着灯、可以随时进来哭一哭、说一说、求一求的心灵驿站。她的教义,不在经卷,而在那一柱柱升起又散去的烟里,在那些被反复摩挲、油光发亮的签筒和膝盖下的蒲团上。
有趣的是,这种“响应性”在今天,正以新的形式流淌。我注意到,在年轻人聚集的网络空间,六月十九的“祈福”变得轻巧而抽象。他们在社交平台发布一张电子莲花或一盏心灯,配文“平安喜乐”;他们或许不会去寺院,却可能在某个冥想App里,跟随引导进行几分钟“慈心观”的练习。仪式被极大简化,甚至符号化了。那种肉身亲赴、汗流浃背的集体体验在减弱。你很难说这是退化还是演进。一方面,它似乎剥离了传统的厚重感,有流于形式之虞;但另一方面,它又以一种更个人化、更内在的方式,延续着那份寻求慰藉与连接的核心渴望。那枚“祈愿”的种子还在,只是播撒的土壤和生长的形态,随着时代的季风改变了。
这么一想,我似乎又回到了那个潮湿的清晨,回到外祖母汗湿的蓝布衫旁。如今的寺前,抢头香的人依然踊跃,但或许也多了不少只是静静驻足、拍一张烛火通明的照片的年轻面孔。那股混合着栀子、青苔与线香的复杂气味,或许也被更多香水与防晒霜的气味稀释。然而,穿过这所有变迁的形式,我仿佛依然能看见同一条河——一条由无数个体具体的焦虑、希望、感恩与无奈汇成的、温暖而浑浊的、生生不息的河流。人们将各自的心事,像折纸船一样,轻轻放入这条名为“信仰”的河流,看着它摇摇晃晃地漂远,至于它最终会抵达哪里,似乎已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放入”这个动作本身,它意味着在无常的生涯里,我们依然愿意相信存在一种倾听,一种慈悲的秩序,并借此获得继续渡河的那一点点力气。
那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终于穿透氤氲的香云,照亮大殿匾额上“慈航普渡”四个金字时,外祖母往功德箱里塞了几张折得很小的毛票,然后按住我的头,让我也鞠了三个躬。她没要我许什么具体的愿,只是低声说:“让菩萨看看你,记得你就好。”许多年后,我才咂摸出这句话里的智慧:或许最朴素的祈福,并非索求,而仅仅是一种存在感的确认——在这浩瀚的宇宙与匆忙的人间,有一个渺小的我,在此刻,被看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