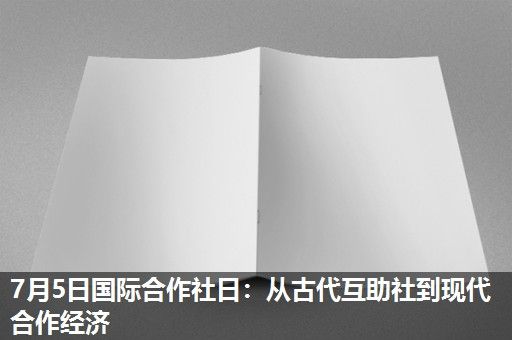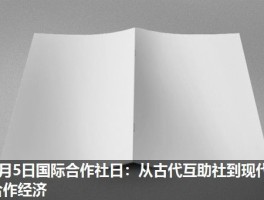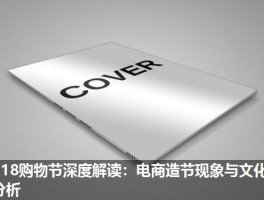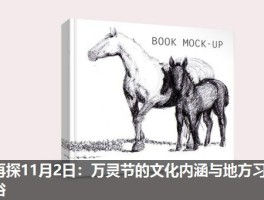记得去年夏天,在川西高原的一个小村子里,我遇到几位正在互助收割青稞的老人。没有合同,没有计件,谁的田熟了就一起先去谁家。休息时,喝着手打的酥油茶,一位阿妈用我不太能听懂的藏语夹杂着汉语说:“日子,一起走,就不重。”那时夕阳正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和身后的青稞田、远山叠在一起。我忽然有些恍惚,这个场景,和我正在电脑里分析的、那份充斥着“股东权益”、“投资回报率”的所谓“社区团购合作社”的商业计划书,仿佛来自两个宇宙。
这大概就是我一直以来的困惑,或者说,执念。我们谈论“合作”,从上古的篝火旁到今天算法的云端,那个最核心的东西——那个让人感觉“日子不重”的东西——还在吗?它是在进化,还是在被悄悄替换?
说起源头,历史书里总会提到那些古老的互助形式。中国的“义仓”,欧洲的行会,非洲的“储蓄圈”。但我最被打动的,不是制度本身,而是一种近乎本能的“有限信任”。我曾在徽州的族谱文献里,看到关于“轮收制”和“计谷捐输”极其繁琐的记录,谁家出了多少力,谁家借了多少粮,秋后如何补偿,一笔笔,清楚又计较。这和我理想中那种无私的、田园诗般的互助相去甚远。但恰恰是这种“计较”,让我觉得真实。早期的合作,并非建立在浪漫的利他主义上,而是建立在清晰的边界感和对等交换的预期上。它的精神内核,是一种在匮乏中生长出来的、清醒的共生智慧:我知道我的,我也知道你的,我们在一起,能活得比一个人好那么一点。这种智慧很朴素,不宏大,甚至有点“小气”,但扎实。
可后来,事情起了变化。当罗虚代尔的工人们举起“公平先锋”的旗帜,将这种朴素智慧系统化、原则化时,一个幽灵——资本的幽灵——也悄然进入了房间。合作运动从此背负上双重使命:既要对抗外部资本的侵蚀,又要防止内部滋生新的剥削。这几乎是一场永恒的走钢丝。我的田野笔记里,记录过北方一个奶牛合作社的衰落。起初,大家轮流值班挤奶,统一销售,利润按交奶量返还,其乐融融。后来市场打开了,需要引进更先进的设备,需要专业的营销人才。分歧出现了:是老社员按过去的贡献多占股,还是按新投资额决定话语权?引进的职业经理人,该拿多少薪水才不算“剥削”?吵了三年,合作社散伙,被一家乳业巨头收购了。你看,打败合作的,有时不是外部竞争,正是合作成功后带来的那些新问题:增长的欲望、效率的焦虑、对“公平”日益复杂化的定义。那个清晰的边界,变得模糊、烫手。
于是我们来到了今天。现代合作经济穿着各种新衣:信用合作社成了社区金融的支柱,消费者合作社在有机食品领域风生水起,甚至出现了“平台合作社”这样的新概念,号称要用民主所有制来改造优步和爱彼迎。挑战显而易见,资金、规模、管理专业化……但这些在我看来,都是技术层面的。真正的深渊,是人心与时代价值观的断裂。
我们生活在一个被“个人效能最大化”叙事笼罩的时代。成功学告诉你要做自己的CEO,风险投资鼓励你快速试错、颠覆一切。而合作的核心——协商、妥协、有时为了整体放慢脚步、信任并依赖同伴——几乎成了“低效”和“脆弱”的同义词。我访谈过一位年轻的“平台合作社”倡导者,他满腔热血,想用区块链技术实现完全透明的民主管理。但当他演示那套复杂的投票和贡献值核算系统时,我看到的更像一个极度精密的经济学模型,一个试图用代码确保绝对公平的乌托邦蓝图。我问他:“当成员们对每一个微小决策都要链上投票时,那份基于人情和默契的信任,还有空间吗?”他愣了一下,说那正是他们要克服的“人性弱点”。
坦白讲,我对这种技术至上主义抱有深深的怀疑。它试图用程序的理性,完全取代人际的感性。这让我想起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的小麦合作社,那是北美最大的农业合作社之一。我曾在那里住过一阵子。他们的决策当然也靠投票,但更重要的是每周六早上的咖啡聚会。老汤姆、约翰逊先生,那些种了一辈子麦子的人,坐在那里,聊天气,聊孙子,也聊国际期货市场的波动。决策,很多时候是在这种漫无边际的闲聊中孕育、达成的。他们的信任,不止在合同里,更在共同的记忆、相似的手茧和一起经历过的坏年景里。这不是技术能“赋能”的,这需要时间的沉淀,需要共同体的肌理。
所以,我对数字时代的合作,有种矛盾的看法。一方面,技术无疑提供了新的工具,让跨地域、跨文化的协作成为可能。但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加速那种“计算性信任”的蔓延,把合作关系简化成一串可比较、可交易的数据点。当“合作”变成一个追求效率和回报的优化模型时,它和它所批判的资本逻辑,是不是最终会共享同一套底层思维?这是我的忧思。
这就说到了7月5日,国际合作社日。对我而言,这一天从来不是一个欢庆胜利的日子。它是一个提醒,一个略显沉重的提醒。它提醒我们,在股东价值最大化的浪潮声中,还存在另一种组织生活的可能。它提醒我们,经济可以不只是冰冷的交易,还可以是温暖的互助。但它也提醒我们,这条道路布满荆棘,需要与人性中的自私、短视和时代巨大的惯性不断搏斗。
我记得那天在川西,我问那位阿妈,年轻人出去打工了,这种互助还能传下去吗?她笑了笑,没有直接回答,只是指了指不远处几个正在玩闹的孩子,说:“你看,他们现在是一起玩的。”是的,合作或许不是一套永远坚固的制度,它更像一团火种。制度会僵化、会异化,但火种可以在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方式被重新点燃——可能在古老的麦场,也可能在虚拟的社区;可能依靠精密的章程,也可能只依赖一句“日子,一起走,就不重”的承诺。
文章该结束了,但我脑子里还是那个画面:夕阳,青稞田,重叠的人影。还有那位年轻工程师电脑屏幕上跳动的、代表民主投票的区块链光点。两者之间,横亘着千年的岁月和全然不同的世界。它们能彼此理解吗?我不知道。或许,合作的精神从来不是一座需要抵达的固定城堡,而是一条我们在不同的地图上,各自寻找的、让“日子不重”的蜿蜒小径。你,找到你的那条路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