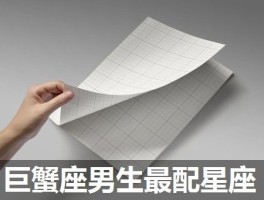整理祖母的老相册时,一张边缘卷曲的黑白照片滑了出来。照片上的婴孩裹在绣花襁褓里,背景是模糊的木格窗。翻到背面,一行褪色的毛笔小楷:“己卯年二月廿七。”我怔了一下。家里人都说祖母是春天生的,具体日子却总是含糊。这个日期,沉静地躺在干支纪年里,对我这个习惯了公历的脑子来说,像一道需要转译的谜语。
我首先得把它“换算”成我能理解的时间。书架上那本红色塑料皮的《百年历书》,是多年前在旧书摊顺手买的,纸页已经泛黄发脆。我小心翼翼地翻到对应己卯年,那应该是1939年。手指顺着农历二月往下找,找到廿七,旁边的公历小字写着:“4月16日”。为了保险起见,我又打开手机,搜索农历转换。试了两三个网站,其中一个弹窗广告多得让人心烦,另一个结果却显示是4月15日。这细微的差别让我有点较真,大概是因为历法换算里“时辰”交接的模糊地带吧。但无论是15还是16,都稳稳落在公历的四月中旬。这么一来,星座的答案似乎呼之欲出了:白羊座,大概是3月21日到4月19日。嗯,按这日子看,祖母大概率是个白羊座。
可这个结论一出来,我反而觉得更有意思了。你看,她的生日固定在农历二月廿七,但对应的公历日子每年都在浮动。如果某年农历闰了月,或者节气推移,这个日子落到公历4月20日之后也说不定。那么,按照星座的说法,她可能就成了金牛座。一个人的“星座性格”,难道会因为这阴晴圆缺的历法浮动而改变吗?这么一想,星座那种按月份划定的、斩钉截铁的论断,在农历这种流动的时间体系面前,忽然显得有点“水土不服”。它描述的更像是一个僵硬的、西方式的太阳轨迹区间,而不是东方语境下,与月亮、节气紧密相连的,更柔韧的生命节律。
不过,琢磨的乐趣也就在这里。我试着把“己卯年”这个标签,和“白羊座”这个标签,放在一起把玩。己卯,天干是“己土”,地支是“卯木”。按我那点粗浅的理解,己土是湿润包容的田园之土,卯木是柔韧生发的花草之木。这组合听起来,该是内敛、滋养、带着点文气的。可白羊座呢,火象,开创,行动力强,总被说成冲锋陷阵的战士。一个听起来像江南园林,一个听起来像驰骋草原。但奇妙的是,它们并非不能共存。或许,那己土的包容,能稍稍中和白羊的急躁,让冲劲更有韧性;那卯木的生发之力,又正好呼应了白羊春天般的生命力。我祖母一辈子操持大家庭,对外待人接物极其宽厚(这是己土吗?),但决定家里大事时,那份果决和担当,回想起来,倒真有几分说干就干、不惧艰难的劲头(这又是白羊吗?)。
这让我想起我的朋友小景。他就是4月16号出生的标准白羊座。大家印象里的白羊座,风风火火,脾气一点就着。可小景偏偏是个慢性子,说话温和,最喜欢的是侍弄花草和临帖写字。有一回我们聊起星座,他笑着说:“是啊,我也觉得不像。但你知道吗,我唯一着急上火、非要立刻马上做成的,就是当年辞了职,非要自己开那个小工作室。”他说那一刻,心里就像有团火拱着,什么稳妥、计划都顾不上,就想着“必须开始,就是现在”。工作室后来经营得不错,他也回归了平日里喝茶养花的闲适。你看,那白羊的特质,或许并非时刻写在脸上,而是蛰伏在骨子里,在某个关键的选择时刻,才猛地蹿出来,完成一次属于它的“开创”。
所以,回到祖母的那个生日。我最终也无法确知,公历1939年4月16日那天,太阳是否精准地运行在白羊座区间。但这探寻本身,已经带我走了一段好玩的旅程。时间被不同的文明切割成不同的刻度,我们因此被贴上“己卯”、“白羊”等等标签。这些标签或许能勾勒一些模糊的群体轮廓,却永远框不住一个个具体的人。就像我祖母,她的生命质地,远比“土”与“火”的简单相加要复杂、深厚得多。那本老黄历和星座手册,或许只是我们用来理解世界与自我的、两套不同的话语。而真正鲜活的,是那个在惊蛰与春分之间降生的人,如何带着她所有的矛盾与和谐,在具体的岁月里,活出了独一无二的故事。想到这里,那张老照片上的婴孩,在我眼中似乎又清晰生动了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