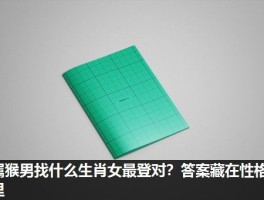最近茶余饭后,又听人提起那句老话,说是“十羊九不全”。话音落下,席间便有些微妙的沉默,目光若有若无地瞟向几位在座的亲朋。我那位属羊的姨妈,倒是抿嘴一笑,自顾自夹了一筷子菜,从容得很。这场景见多了,反倒让我想起这些年遇到的、属于这个生肖的人们。他们像散落在时间长河里的羊群,毛色不同,步态各异,走过的草地更是天差地别。
细数起来,从上一个甲午战后算起,到我们以为很“近”的2015年,完整的农历羊年,其实也就这么六个:1955年,1967年,1979年,1991年,2003年,还有2015年。你看,六十年的光景,被这六个年份轻轻一标,脉络忽然就清晰了些。这不是一份冰冷的名单,更像是一扇扇窗,窗外是不同的风雨和日头。
先说那头最年长的“羊”,1955年的。我姨妈便是。她的人生开场,恰逢一个百废待兴又暗流涌动的年代。关于“属羊命苦”的喟叹,在她身上并非虚言,但绝非定论。少年失怙,中年下岗,人生的重锤接二连三。我曾问她,知不知道自己属羊,所以民间说法不好?她手里打着毛线,头也不抬:“知道啊,小时候街坊就说。可日子是苦是甜,是自己过出来的,又不是属相过出来的。” 她的坚韧,是一种被生活磨出来的、沉默的韧性,像石头缝里长出来的草,不张扬,但你也别想轻易踩死它。她那一代人,信“奋斗”多于信“命运”,生肖对他们而言,更像是一个便于记忆的出生记号,或是在遭遇不幸时,旁人一句略带宿命论的、无力的安慰。真正的重量,来自时代落在个人肩上的尘土。
话分两头,到了1979年那只“羊”,境况就大不同了。改革开放的春风,他们是真切吹到了的。我一位79年的朋友,常自嘲是“喝改革奶水长大的羊”。他思维活络,敢于闯荡,身上兼具了属羊人常被提及的“温和细腻”与时代赋予的“进取机敏”。你说他信生肖吗?他信一点,觉得羊的温和能让他在人际关系里获益,但他绝不信“命不好”那套。他的口头禅是:“市场又不看你属什么,只看你能做什么。” 在他这里,生肖性格成了一种可供自我挖掘、甚至主动运用的“软技能”。这是承平年代、经济上升期赋予一代人的底气——他们开始有闲心,也有自信,把古老的符号拿来玩味,而非敬畏或恐惧。
这差别很有意思。55年的羊,可能要用一生去消化和抵抗“命不好”这个标签所象征的、真实的苦难;而79年的羊,已经有能力把这个标签撕下来,反过来调侃它、解构它。时代的河床,决定了河流的表情。
再说那1991年和2003年的羊,就更“飘”了。91年的,是互联网的原住民,他们的世界比父辈宽广太多,也破碎太多。“属羊”这个身份,在星座、MBTI、各种亚文化标签的冲击下,影响力大大稀释。我认识一个91年的姑娘,她说她知道这个说法,但感觉“像听一个遥远的传说”,毫无切肤之痛。她更愿意用“INFJ”或“水瓶座”来定义自己。生肖对她而言,是春节家庭聚会时,长辈们用来打开话题的、略显过时的“社交货币”。而03年及之后的羊,还在成长中,他们活在信息爆炸的茧房里,属相不过是出生证明上一个无关紧要的字段。那个“命不好”的古老诅咒,在他们丰富多彩的人生选项面前,显得苍白又滑稽。
绕来绕去,其实我想说的是,我们谈论“属羊”,究竟在谈论什么?在我看来,生肖这玩意儿,从来不是一本写好的命运剧本,它更像一面镜子,或者一枚古老的印章。镜子照出的,是谈论它、相信它、或反对它的那个人,他自己的内心恐惧、期望与认知局限。而印章盖在不同时代的画卷上,印迹(那十二个动物)是固定的,但每幅画卷的内容(个人的具体人生)早已千差万别。
那个“命不好”的说法,溯源起来很复杂,有历史偶然,也有古代社会对女性(尤其是所谓“羊女”)的某种扭曲投射。但它能流传至今,无非是因为人生实苦,人们总需要为苦难找一个简单易懂的“原因”,好让无常显得有常,让随机显得有序。属羊,不幸成了这个情绪的出口之一。但以我的观察,我身边那些属羊的亲友,他们的幸福与否,跟这个属相关系不大,倒是跟性格、选择、努力以及一点点运气关系极大。我的姨妈晚年儿孙绕膝,生活平静满足;那位79年的朋友事业有成,但也为中年危机烦恼;91年的姑娘正在为职业选择焦虑。你看,他们的悲喜,如此具体,如此“人间”,哪是一个“羊”字可以涵盖的?
所以,下次再有人提起那份羊年的名单——1955、1967、1979、1991、2003、2015——我看到的,不再是几个孤立的年份或一个单薄的标签。我看到的是六片不同的天空,六茬不同的草木,和一群在各自命运牧场上,低头吃草或抬头仰望星空的、生动的生命。他们温和,或许也倔强;他们顺服,或许也暗藏反骨。这才是生活的真相,复杂,微妙,拒绝被任何一个简单的符号所定义。
属相只是一件穿了一生的、无形的文化内衣,舒服与否,只有自己知道。而人生的辽阔与否,从来取决于行走的双脚,而非内衣上绣着的那个图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