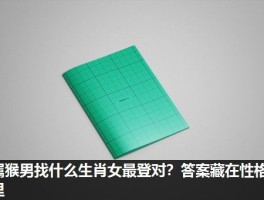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个秋雨绵绵的午后,我和几位老友围坐在茶馆的窗边。窗外是湿漉漉的灰瓦檐角,窗内是氤氲的茶香和漫无边际的闲谈。不知怎的,话题就绕到了各自的出生时辰上。在座三位都属狗,月份却大不相同:王哥是正月里的“开春狗”,李姐是盛夏七月的“伏天狗”,而老陈则是腊月末尾的“守岁狗”。听着他们半是调侃半是认真地谈论各自性格的来由,以及那些被归因于“月份”的人生转折点,我忽然有些出神。杯中的茶叶缓缓沉浮,像极了许多被文化标签轻轻覆盖,内里却奔腾不息的人生。
话说回来,关于属相与月份的交织,坊间的“定式”实在太多。我倒觉得,与其把它当成一副不容更改的命牌,不如看作一幅用文化颜料晕染过的“性格底稿”。在不同的月份光线下,这幅底稿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色调与笔触。以我这二十多年杂七杂八的观察和阅读来看,有几个月份的对比,格外有意思。
我总对春天出生的属狗人,抱有一种近乎偏爱的关注。尤其是农历二三月,惊蛰与清明前后。这个时节,天地解冻,草木抽芽,生命里有一股压抑不住的、向外探求的冲动。我舅舅就是典型的“二月狗”。他年轻时是个乡村教师,却有着一身与身份不甚相符的“不安分”。恢复高考那年,他已近而立,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所有人都觉得他该守着那份安稳的教职,他却像嗅到了春风里第一缕新泥气息的狗一样,躁动起来,没日没夜地复习。我母亲回忆,那时他屋里深夜的煤油灯光,成了村里一景。后来他真考上了省城的大学,人生轨迹彻底转向。他身上有种属狗人共通的忠诚——但那忠诚似乎更多是献给内心某种“生发”的信念,而非固化的环境。春狗,给我的感觉,他们的“看家”本能,守护的往往不是一个具体的院落,而是自己心里那片亟待破土的理念的苗圃。他们的命运里,有一种“破”的勇气,当然,也必然伴随着“立”之前的颠簸与风险。
与春日的勃发截然相反的,是深秋时节,譬如农历九、十月降生的狗。此时万物收敛,天地气象变得肃穆、清朗。我一位忘年交,便是“九月狗”。他是位极出色的古籍修复师,一生伏案,与虫蠹、水渍、破碎的时光为伴。他的性格,像极了秋天午后透过高窗落在宣纸上的光——稳定,澄澈,有温度却不灼人。做事呢,是出了名的“慢工细活”,一个复杂的卷轴拆解,他能不声不响研究半个月方案。我曾感叹他这份沉静得惊人的耐心,他笑了笑,用带着老茧的手指轻轻拂过案上一片待补的绢面,说:“急什么呢?该熟的果子,秋风自然会把它染红;该还原的旧事,你得顺着它的纹路,一寸一寸地往回走。” 在他身上,属狗的忠诚、尽责,演化成了一种对“过程”本身的极致尊重与守护。秋狗的命运之路,往往不是广阔的草原,而是一条深邃、需要步步印证的林间小径。他们的收获,来得可能不迅猛,却有着被时光充分酿造的、坚实的甜。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那个常被忽略、却又在我观察中极为独特的群体——那些出生在月份“交界”或“闰月”里的人。我的一位表侄女,就生在闰六月。她的性格里,常常呈现出一种有趣的“摇摆”与“融合”。有时她雷厉风行,充满行动力(带点盛夏的炽热),有时又莫名地陷入一种审慎的、近乎多虑的徘徊(仿佛沾染了后一个月初秋的预兆)。她自己也常调侃,说身体里好像住了两只狗,一只想撒欢奔跑,一只想趴在门廊下静静观望。这听起来像是玩笑,但我却觉得,这或许正是文化历法设置中那些“缝隙”所赋予的微妙礼物。他们的“剧本”不那么板正,反而多了些自我对话、自我矛盾的张力和空间。命运对他们而言,或许少了一分“理所当然”,却多了一分需要自己去辨认、去整合的复杂意趣。
当然了,聊了这么多月份带来的“底色”,我内心最想分享,也最确信的一点是:所有的这些,都仅仅是一幅“底稿”而已。我常常想起那个茶馆午后的李姐,“伏天狗”。照一些说法,盛夏之狗,易心浮气躁,劳碌多艰。李姐的前半生似乎应和了这点,下乡,返城,在工厂三班倒,丈夫早逝,她一人拉扯孩子,日子是拧得出汗水的。可她身上有股子劲,是任何标签都贴不住的。五十岁那年,工厂效益不好,她索性提前退了,用极少的积蓄,租了个小门脸,开了间早餐铺子。不是简单的粥粉面,她专门做我们当地几近失传的一种手工糯米糕。每天凌晨三点起身,选米、磨浆、烧柴火、上蒸笼…那糕点的滋味,成了整条街区的念想。去年,她居然把铺子开到了古文化街上,成了“非遗体验点”。你说,这是“伏天狗”劳碌命的延续吗?我觉得不完全是。这更像是一个生命,在汲取了所有暑热与艰辛的能量后,自己选择将它淬炼成灶膛里那团温暖、持久、能孕育出甜香的火焰。
这便是我对所谓“出生月命运”最深的感触。它或许描绘了我们性格最初的倾向,像不同窑温烧出的陶器坯体,有的酥松些,有的紧实些;它也仿佛预设了我们早年可能遭遇的“气候”,是温润春风还是凛冽霜雪。但最终,这件器物会成为什么——是日用的粗碗,是观瞻的瓶尊,还是养着一株绿植、别有生趣的盆盂——靠的是我们在时代的长河里,选择如何被冲刷,选择盛放什么,又选择向世界呈现怎样的釉彩。我自己的人生里,也有过几次看似“背离”某种文化预期的选择,其中的得失甘苦,此刻回想,都成了独属于我生命陶器上的纹路。
窗外的雨不知何时停了,有一抹夕阳的余晖,正巧落在我们当时喝茶的那张木桌上。那光线温润地铺开,让我想起舅舅复习时的那盏煤油灯,想起修复师朋友手下渐次清晰的古画,想起李姐蒸笼里升腾起的那片白蒙蒙、香喷喷的雾气。你看,无论是春日的萌动,秋日的沉静,还是夏日酷暑与闰月迷思,最终都融汇成了具体的人,在具体的生活里,踏出的那一个个深深浅浅、方向不一的脚印。
所以,若你问我,属狗的你,生于某月,命运究竟如何?我大概只会为你再斟上一杯茶,指着窗外那株历经风雨、却每年都按时发芽、又在秋日落尽黄叶的老树,轻轻地说:瞧,它的年轮里,藏着每一季的风雨,也藏着它向着阳光,每一次固执的、向上的生长。你的命运,终究在你的脉管里奔流,在你的足下延伸。而那月份,不过是漫长故事里,一个美丽而朦胧的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