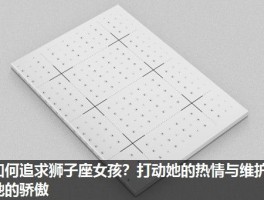我书架的顶层,靠左的位置,有一本红色塑料封皮的《毛主席语录》。它并不显眼,挤在一排更厚的理论著作和史料汇编旁边。塑料皮已经泛白,边缘磨得起了毛,像一件穿旧了的确良衬衫的领口。书页很松,稍微一抖,里面会掉出一些东西:可能是一张九十年代粮票的残角,也可能是我父亲用蓝色圆珠笔,在空白处抄录的一首辛弃疾的词。这本书自我有记忆起就在那里,它更像一个沉默的、来自旧日生活的摆件,而不是一本书。偶尔,在12月某个阴冷的下午,我会把它抽出来,不是为了读,只是为了感受那种纸张特有的、混合着旧塑料和灰尘的、几乎有了重量的气息。这种气息,就是我认知里关于“毛泽东”最初的、也是最顽固的底味——它不完全是历史的硝烟,更像一种凝固了的、日常化的、却又挥之不去的存在。
话头既然从这里开始,我就想谈谈“存在”本身——不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他,而是作为一个不断被涂抹、被阐释、最终变得有些光怪陆离的文化符号的他。我的童年,他的形象是绝对均质的。教室里、堂屋正中、甚至搪瓷杯上,都是那张标准像:饱满,慈祥,目光望向一个所有人都被暗示存在的、辽远的未来。那是一种不容置疑的、带有体温的神圣。这种神圣,在成长过程中,被八九十年代涌入的各种思潮冲刷、侵蚀,开始变得斑驳。我记得大学时,和几个同学在熄灯后的宿舍里,压低了声音争论《河殇》,争论那些刚刚解禁的文学作品里影影绰绰的苦难。那时,符号的油漆开始剥落,露出了底下复杂甚至狰狞的木纹。我们有一种打破神像般的、混合着恐惧与兴奋的激动。
说来也巧,我后来从事文化传播工作,很长一段时间接触过宣传画和老电影的数字化修复。在冰冷的服务器机房,看着那些高分辨率扫描的、每一道笔触都清晰无比的工农兵形象,以及画面中央永远挥手指引方向的领袖,我感受到的是一种巨大的抽离。神圣感退潮了,留下的是精湛的构图技巧、饱和到近乎暴烈的色彩,以及一种高度程式化的美学语言。那个符号,在技术的放大镜下,成了一件可以冷静分析的“作品”。这大概是一种祛魅的过程。但有意思的是,祛魅之后,并没有导向简单的虚无。近些年,在网络空间,这个符号又被赋予了新的、截然不同的生命。它时而出现在戏谑的表情包里,时而又在某些社会议题的讨论中,被青年一代引用其语录,作为一种对当下不平等现象的、带着怒火的批判武器。那个“反叛者”、“打破旧世界”的毛泽东,似乎被从复杂的革命史中单独抽取出来,重新擦亮,用以映照新时代的焦虑。
这种符号的流变,或者说漂移,让我时常陷入一种矛盾的沉思。我们缅怀的,究竟是哪一个毛泽东?是历史中那个做出了一系列艰难、甚至残酷抉择,深刻塑造了国家肌体与民族心理的政治家与战略家?还是那个被不同时代、不同群体依据自身诉求,不断重新想象和塑造的文化意象?我的工作让我深知,传播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滤镜,它会强化某些光谱,而过滤掉另一些。所以,我越来越警惕任何单一的、斩钉截铁的论断。对于他,或许只能用一种地质学家般的眼光去看待:他和他所代表的时代,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社会最深、最厚也最纠结的地质层之一。你无法绕开,每一镐挖下去,可能触及富矿,也可能引发塌方。
这就要说到,我为什么在今天——他的诞辰——会想起他的“矛盾论”里的只言片语。不是全篇,不是体系,就是“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这句话。年轻时读,觉得是枯燥的哲学教条。但活到中年,处理过无数棘手的工作,观察过各种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后,我反而时常觉得,这句话提供了一种最质朴也最有效的认知框架。面对一个复杂的项目,或者一个争议性的公共事件,我常常会下意识地逼自己停下来,问:这里面的主要矛盾是什么?矛盾的主要方面又在哪里?它和次要矛盾是如何转化的?这个方法,当然不能给出完美的答案,但它像一把不算锋利却足够结实的冰镐,帮助你在信息的冰川上凿出几个踏脚的坑,不至于滑入情绪或偏见的深渊。这是一种剥离了具体政治指向的思维工具,是他留下的、我认为仍在“活着的遗产”中比较坚韧的一脉。它不承诺幸福,只承诺一种面对复杂时的清醒可能。
所以,你问我今天的个人情感究竟是什么?坦白说,没有澎湃的崇敬,也没有愤懑的批判。那更像一种站在冬日江边的感受。你知道这江水的深处,沉积着无数的故事、力量、泥沙乃至伤痕。它曾经改道,曾经泛滥,也曾灌溉出沃野。它沉默地流着,而你就站在此刻的岸边,带着你全部的私人记忆——那本磨毛了的红宝书、父亲抄词的笔迹、宿舍夜谈的悸动、机房屏幕上的高光——试图去理解这江流的来路,并猜测它未来的去向。风很冷,江面广阔,你看不到对岸的细节。你手里没有鲜花,也没有投掷的石块。你只是站在那里,知道这江水与你有关,知道它的温度已经渗入了你脚下的土地,也构成了你生命气象的一部分。这种关联,不是节日的,而是日常的;不是喧哗的,而是静默的。它让这个日子,对我而言,更像一个用来丈量自己与历史之间距离的、安静的刻度。我合上那本语录,把它放回原处。灰尘在窗格透进的光柱里缓缓浮动,一切如旧,一切又都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