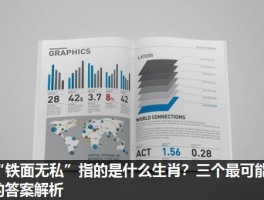最近有位朋友喜得麟儿,特意来问我,说孩子生在龙年尾巴上,这属龙是板上钉钉了,可往后该怎么跟人介绍他的岁数呢?是按着出生证明上的日子一天天数,还是跟着家里的老人,一口一个“虚岁”地叫?这问题像颗小石子,在我心里荡开了一圈圈涟漪。可不是么,给一个属龙的孩子,或者说给任何一个在中华文化脉络里生长的人算年龄,从来都不只是一道简单的减法题。
这事儿让我想起我小姨。她是个顶有意思的属龙人,身份证上的年份明明写在那里,可她心里自有一本账。每逢家族聚会,论起长幼次序或是聊到年纪,她总会不紧不慢地纠正:“哎,那是周岁的说法,按咱老规矩,我得算虚岁,大着一岁呢。”起初我们这些小辈觉得费解,后来倒也成了家宴上一段固定的、带着温情的拌嘴节目。你看,就在这“一周一虚”的拉锯里,两种时间观悄然浮现了。以我的体会,周岁像瑞士产的精密腕表,分秒不差地丈量着你在地球上存在的光阴;而虚岁呢,更像咱们的老黄历,它计算的是生命的“季”。它有点蛮横,也有点温情,愣是把你在母腹中蜷缩的那段混沌岁月,也慷慨地认作了一轮阅历。你一落地,它便大笔一挥:喏,这人已经“经历”过一个春秋了。这算法里,有种“生命优先于时间”的古朴哲学,承认你存在本身,就是一种饱满的经验。
说到属龙人的年纪,总绕不开那个金光闪闪又让人有点心里发毛的节点:本命年。我有个朋友,也属龙,去年正好是她的第二个本命年,周岁二十四,虚岁二十五。春节还没到,她妈妈就从老家寄来了一整套红内衣裤、红袜子,还有编织精细的红绳手链。她一边拆包裹一边跟我视频,嘴上嫌弃着“太俗了”、“穿了也不见得有用”,可镜头一转,除夕夜她还是乖乖把那身行头套上了。她当时跟我说:“其实我知道都是心理作用。但你说怪不怪,一想到自己‘虚岁’都二十五了,心里还真就咯噔一下。好像按那个算法,我被时间推着,得更‘像个大人’才行。” 你看,这“虚”出来的一岁,无形中竟成了心理上的一个加速器,一种社会时钟的内化。它提醒你的,往往不是生理的刻度,而是文化的、伦理的期待——“你都虚岁二十五了,该如何如何了”。
这么一想,虚岁的压力感,恐怕是越到中年越显山露水。我父亲有位老同事,我叫他陈叔,也属龙。前两年他张罗做寿,家里却为过哪个岁数起了点小争执。陈叔的身份证上写着四十九,可他坚持要按虚岁过五十整寿。他儿子觉得,现在都兴过周岁生日,五十岁是个大坎,明年过才正宗。陈叔那次喝了点酒,话也多了起来,他拍着桌子说:“你们年轻人不懂!我这虚岁五十,是活明白了一件事——这五十年,是算上在我娘肚子里听她哼曲儿、跟我爹怄气的那一年!那一年,算数!” 这话让我怔了半天。在他那里,虚岁不再是模糊的添头,而是一份对生命源头的、充满情感的回溯与确认。那多出来的一岁,是根,是来处。周岁标记的是独立的个体时间,而虚岁,隐隐串联着血脉的承续。
等到了花甲之年,这差异又变了一番味道。我曾在老家见过给一位虚岁六十一的“老龙”祝寿的场面。堂屋里高悬的寿幡上,明明白白写着“六秩晋一荣庆”。按周岁,他才刚刚踏进六十的门槛呢。可来贺寿的亲友,尤其是老一辈,都认这个“晋一”。攀谈起来,他们会说:“过了年就是六十一的人啦,福气厚,看得开!” 在这里,“虚岁”似乎又成了一种祝福的修辞,一种对跨越时间门槛的隆重宣告。它不再催人,反而有了种“赚到了”的从容和喜悦。仿佛多算的这一岁,是老天爷发的红利,是历经风霜后应得的一份宽宥。
这么漫无边际地想来,我发觉给属龙人算年龄,就像在两种时间维度里 quietly穿梭。一种是公转,是地球绕太阳画的、全世界通用的那个冰冷而公平的圆圈;另一种是自转,是家族记忆与文化血脉内部生成的、带着体温和故事的循环。我那位刚当爸爸的朋友,将来大概也会面临这种甜蜜的烦恼:当孩子哭闹着要按周岁年龄买半价票时,他得解释;当爷爷奶奶按虚岁给孩子压岁钱、念叨着“又长了一岁要更听话”时,他也得理解。
所以,下次再有人问我,属龙的人到底多大年纪,我可能不会立刻给出数字。我或许会反问他:“那你想知道的是故事里的岁数,还是合同上的岁数呢?” 前者连着根,浸着情,可能有点“不精确”;后者白纸黑字,一目了然,却也失却了些许生命的毛边与温度。属相是龙,或是其他,其实都一样。我们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生账本,向来都是两套算法并行不悖的。而意识到这一点,或许就是理解自身文化处境的一个小小的、却不可或缺的起点。至于我那属龙的小姨,明年家庭聚会,我打算主动用虚岁敬她一杯——就当是,对她那份固执的、对生命不同算法之温柔的守护,致以我个人的一点理解吧。